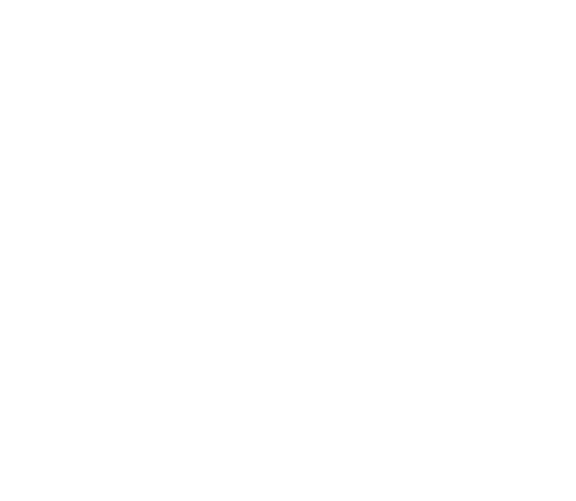止痛药销量曾一度超越伟哥,背后家族隐藏大秘密?
前言:萨克勒家族在世界各地捐助了无数的艺术建筑和研究机构,然而其家族企业普渡生产的止疼药OxyContin却在美国产生出数以百万计的药物成瘾者。而这,都要归因于萨克勒家族对止疼药的无原则营销。
萨克勒家族的艺术大手笔投资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北侧是一片广阔而通风的大厅式建筑,埃及政府赠送美国的典德尔神殿陈列于此。这座砂岩纪念碑落成于两千年前的尼罗河边。埃及政府将其作为礼物拆解运到美国并再次组装起来。安放典德尔神殿的萨克勒馆于1978年向公众开放,也是美国大慈善家萨克勒家族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出生于布鲁克林的亚瑟,莫蒂默和雷蒙德——萨克勒家族的三兄弟都是医生,在一生中捐款建设了很多设施,其中许多以其姓氏命名的机构今天依旧耳熟能详:华盛顿的萨克勒美术馆、哈弗大学的萨克勒博物馆、古根海姆的萨克勒艺术教育中心;卢浮宫的萨克勒馆。此外还有坐落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十多所知名学府的萨克勒研究所和相关设施。萨克勒家族被授予了各种教授职位,也包揽了各项医学研究。艺术学者托马斯·劳顿(Thomas Lawton)曾经将亚瑟(Arthur)比喻为“当代先驱”。1987年在亚瑟去世前,他告诉他的孩子们,“让你离开时的世界比来时更美好”。
莫蒂默于2010年去世,而雷蒙德也于今年早些时候去世。这些兄弟留给他们继承人的,不仅是为人称道的慈善传统,还有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亚瑟的女儿伊丽莎白位居布鲁克林博物馆董事会,她捐赠成立了伊丽莎白A.萨克勒女权主义艺术中心。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和乔纳森在耶鲁大学癌症中心任教授。理查德说:“我父亲让乔恩和我都相信慈善事业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莫蒂默36岁的女儿玛丽莎·萨克勒(Marissa Sackler)以及莫蒂默的第三任妻子特雷莎·罗琳(Theresa Rowling)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的孵化器Beespace,后者对很多慈善基金提供了支持。玛丽莎最近指出,她发现“慈善事业”这个词已经过时。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当1880年大都会博物馆最初落成时,作为其受托人之一的律师约瑟夫·切特(Joseph Choate)在落成仪式上发表了演讲,宣扬了慈善事业的不朽:“都想一想,很多业内的百万富翁将获得多大的殊荣。你所做的,只是听取我们的建议,把猪肉变成瓷器,把原材料变成无价的陶器,把粗犷的矿石变成精美雕塑的大理石“。通过这样的转变,许多财富就会转化成永久的公众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财富会被遗忘,但以捐献者命名的建筑物却永远存在。据《福布斯》报道,萨克勒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财产净值大约为13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洛克菲勒或梅隆家族。
真实的资产:止痛药帝国
萨克勒家族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在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财富的来源讳莫如深。虽然萨克勒家族经常公开谈及慷慨慈善的问题,但他们几乎不会公开谈论家族企业。其家族企业普渡制药公司是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私人企业,研发推出了处方止痛药OxyContin。1995年该药品上市后,OxyContin被业内誉为医疗突破,这种麻醉性药物可以帮助患有中度至重度疼痛的患者。该药成为普渡制药公司的一枚重磅炸弹,据报道,公司营收约为350亿美元。
但是OxyContin是一种有争议的药物。其唯一的活性成分是羟考酮,是大名鼎鼎的海洛因的化学表亲,其强度高达吗啡的两倍。过去,因为众所周知这种合成药物是从鸦片中提取的,由于这类药物有一定的成瘾性,除了针对癌症引发的疼痛和用于临终治疗之外,医生一直不愿意开阿片类药物用作止痛之用。曾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的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表示,“几乎没有药物像阿片类药物一样危险。”
普渡制药公司针对OxyContin的推广发起了一系列营销活动,试图反对固有的态度,改变医生对阿片类药物的处方习惯。该公司之所以资助研究工作并并提高医生报酬,就是为了说明关于阿片类药物成瘾性的担忧被过分夸大,OxyContin可以安全用于更多疾病的治疗。医药销售代表将OxyContin称之为一种“可以长期使用”的药物,而数百万患者也发现该药物是止痛的绝佳良药。但是很多患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依赖性,而一旦减量,虚弱感就随之而来。
争议中的止痛药:成瘾还是不成瘾?
自1999年以来,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OxyContin和其他处方阿片样药物有关的使用过量。许多吸毒者因为发现处方止痛药太贵或太难获得,已经转向使用海洛因。据美国成瘾医学协会介绍,在吸食海洛因成瘾者中,有五分之四的人都是从使用止痛药开始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数据表明,每天有145名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布兰迪斯大学阿片类药物政策研究协作联合主任安德鲁·科洛德尼(Andrew Kolodny)与数百名患有阿片类物质成瘾的患者合作进行阿片受体研究。他表示,虽然主要是OxyContin以外的阿片类药物导致了许多成瘾症,但是由普渡制药公司精心设计的处方文化逐步导致了危机的产生。科洛德尼指出,“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些所有阿片类药物的处方趋势,可以看出在1996年,相关处方量陡然增长。这不是一种巧合。当年普渡制药公司发起了多方运动,误导了医疗界关于这个风险的认识问题。“当我问及科洛德尼普渡制药公司该对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负有多大责任时,他回答说:”最大的份额“。
尽管你可以在数十座建筑物上找到萨克勒家族的名字,但普渡制药公司的网站却鲜有这个家族成员的身影,公司董事会的名单并没有包含萨克勒家族三代人的八名家庭成员。杜克大学医学院前主席,精神病学教授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指出,“我不知道世界不同地方有多少房间是以萨克勒家族命名的。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成果的缩影。但是,终归他们是以牺牲数百万成瘾者的生活为代价获得了这笔财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摆脱了这一污点。”
雷蒙德·塞克勒和贝弗利·塞克勒
“萨克勒博士自认为也被认为是萨克勒家族的族长,“代表亚瑟·萨克勒子孙的律师曾经观察过。亚瑟是一位门牙有缝的指挥大师,曾师从荷兰精神分析师约翰·汉姆·范奥西森(Johan HW van Ophuijsen),萨克勒自豪地将范奥西森描述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门徒”。亚瑟和他的兄弟都是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移民的孩子,在大萧条时期的布鲁克林长大。他们三人都进入医学院深造,并在皇后区的Creedmoor精神病中心合作出版了一百五十本学术论文。以亚瑟自己的话说,他对“自然和疾病人类秘密”的方式特别着迷。萨克勒家族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方向很有兴趣,例如那些电击疗法和心理分析。
但是,三兄弟真正积累财富的是在商业领域,而非医疗实践。他们向公众分享了创业历程。早在青少年时期,莫蒂默就是高中报纸的广告经理,通过游说切斯特菲尔德发布了一则香烟广告后,其获得了一笔五美元的佣金这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1942年,亚瑟在专门从事医疗领域的小型广告机构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William Douglas McAdams)谋得了一个写作职位,获得的报酬能够支付他的医学费用。事实证明他对这项工作非常擅长,最终亚瑟收购了该机构,并彻底改变了整个制药行业。在此之前,制药公司还没有通过广告宣传的行径。作为一名医生,同时又是一名广告人,亚瑟对于营销的熟知展示了广告狂人般的直觉。他认识到,销售新药物不仅需要吸引患者,而且还需要获得开处方医生的认可。
萨克勒认为医生是无可置疑的公共卫生管家。他习惯说:“相比于国家,我更愿意把自己和家人放在一个同胞医生的判断和怜悯之下。所以在销售新药时,他设计了一种直接针对临床医生的运动,在医学期刊上放置广告,并向医生办公室派发文献。意识到医生受自己同行的影响最大,他引用业内杰出代表来批准他的产品,引用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经常由制药公司承担费用)来佐证效果。在萨克勒手下工作了十年的约翰·卡利尔回忆说:“萨克勒的广告看起来非常严肃,堪称医生与医生之间的交谈。但是这还是广告。“1997年,亚瑟入住医药广告名人堂,其终生成就在于”将广告宣传引入了药品营销“。但艾伦·弗朗西斯指出:”造成制药行业现状的可疑做法都要归因于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
一般而言,广告都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亚瑟营销的技巧有时是一种公然欺骗。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他制作了一个关于辉瑞抗生素西格马霉素的广告:一系列医生的名片,以及“越来越多的医生发现西格马霉素是抗生素治疗的最佳选择”,这等同于让棒球明星米奇·曼托为麦片打广告。但1959年,《星期六评论》的调查记者试图联系名片上的一些医生。发现这些医生根本不存在。
20世纪60年代期间,亚瑟对镇定剂Librium和Valium进行了大量营销。一个关于Librium广告的描绘了一名年轻女子携带一大堆书籍,并建议如果大学新生在离家之后感到焦虑,最好的方式是用镇静剂处理。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受到身份认同感的折磨”,此外还补充说,大学生活带来了“一个关于全新世界的焦虑。“这则广告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此外,萨克勒也对Valium进行了大量推广1965年,一位医生在《心理学》杂志上写道:“我们何时不使用这种药物?”一项活动鼓励医生为那些并没有精神病症状的人开出Valium:“对于没有病理学可证明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Valium。“Valium的制造商Roche并没有对其潜在成瘾性进行深入研究。在该企业与萨克勒合作过的温格尔森(Win Gerson)多年后指出,Valium的营销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部分原因是该药物的效果非常好。格尔森说:“起早就了很多废人,但这种药物是有效的。”到1973年,美国医生每年开出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一亿张,无数的病人开始依赖于镇静剂。参议院曾就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所说的“依赖性和成瘾性的噩梦”举行过听证会。
在运营广告公司时,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还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每个半月出版一次《医学论坛报》,其受众有60万名医生。他自嘲自己既是制药广告公司的负责人又是医学期刊出版社的负责人。但是在1959年,他旗下的MD出版社,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抗生素部门主管亨利韦尔奇(Henry Welch)支付近30万美元,让后者帮忙推广某些药物。有时韦尔奇在发言时,会把某些药物的广告口号插入讲话中去。(这一交易被发现后,韦尔奇被迫辞职了。)当我问及关于韦尔奇的丑闻时,受访者笑了起来,并说:“他被亚瑟选中了。”
1952年,萨克勒兄弟收购了一家小型专利药公司Purdue Frederick,该公司位于格林威治村,主营业务是生产泻药和滴耳液等简单药品。根据相关法律文件每人控股三分之一,但被出版和广告业务缠身的亚瑟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记者Barry Meier在2003年出版的《痛苦杀手:奇迹药物的成瘾与死亡之路》一书中指出,亚瑟对待他的兄弟“根本不像兄弟姐妹,而是对待像小孩一样。“而现在,雷蒙德和莫蒂默成为联合CEO,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60年代初,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特·凯福韦(Estes Kefauver)成立了一个研究制药业的小组委员会且发展迅速。曾经调查过黑社会的凯福韦对萨克勒兄弟特别感兴趣。凯福韦手下工作人员编写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萨克勒帝国有完全一体化的行动,可以在其控制的药物开发企业中有目的地制造出一种新的药物,有关于该药物的临床测试,并从各医院获得有关药物测试的有利报告,有联系方式,有广告手段,并在自己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临床文章以及广告文案,还会通过报纸和杂志上的公开文章进行营销植入。“1962年1月,亚瑟前往华盛顿,与凯福夫小组委员会当面质证。参议员小组对他提出了各种尖锐的问题,但亚瑟是一个强大的对话者——圆滑,冷漠,言语无可挑剔,没有参议员能否定他。萨克勒抓住了凯福韦的一个错误,并说:“如果你受过医疗相关专业的学位培训,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有人质疑一种胆固醇药物会造成脱发等副作用,萨克勒面无表情地讲,“相比于冠状动脉加厚,我宁愿掉头发。”
随着萨克勒家族越来越富裕,他们成了艺术品的常客。1974年,三兄弟向大都会博物馆捐赠3500万美元,用于建造典德尔神殿的翼楼。当年莫蒂默在这里举办了一次奢侈的生日聚会。蛋糕是伟大的狮身人面像的形状,但它的脸已经被莫蒂默替代了。
1987年4月,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73岁时,他让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吉利安掌管整个家庭支出。他口述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我决定自行负责我的遗产问题。”一个月后,亚瑟心脏病发作死亡。家族在大都会博物馆为其举行了追悼会,但亚瑟的孩子们和吉利安就遗产分配问题反复争吵,并因为房产与莫蒂默和雷蒙德争论不休。他们指责吉利安试图窃取他们应得的遗产。根据家庭会议记录,亚瑟的女儿伊丽莎白认为亚瑟隐藏了一些真正的价值投资,因为他不想让莫蒂默和雷蒙德知道。”一位家庭律师告诉孩子们,“两边都没有绝对的胜算。”
亚瑟的后裔仍然拥有Purdue Frederick制药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莫蒂默和雷蒙德也有兴趣购买股份。该公司已经搬到康涅狄格州,最终更名为普渡Purdue Pharma制药公司,在家族的管理下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这样的财富似乎并不多。在两兄弟出价的时候,普渡制药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种新药:OxyContin。
人类种植了罂粟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承认这种植物的疗效。但即便古代,人们都清楚,麻醉药物的功效被其成瘾的危险性所抵消。在1996年出版的《鸦片:历史》一书中,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指出,对于罗马人来说,罂粟是睡眠和死亡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雷蒙德和莫蒂默在普渡制药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开发出一种新型止痛药MS Contin,这是一种具有“控制释放”专利配方的吗啡丸:药物会在数小时内逐步溶入血液。(“Contin”是“连续性”的缩写。)MS Contin成为普渡制药公司历史上销量最大的药品。但到80年代末期,产品专利即将到期,普渡制药公司高管开始寻找一种替代药物。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这是一个神秘,举止略显笨拙的人,其曾经接受过医学培训。理查德于1971年加入普渡制药公司,从担任他父亲的助理开始一路上升。他的名字曾出现在许多医学专利上。1990年夏天,普渡制药公司科学家向理查德和其他几位同事发了一份备忘录,指出MS Contin“面对严重一般性竞争的能力有限,必须考虑其他受控释放的阿片类药物”。该备忘录描述了正在进行的研发工作,是开发一种含有羟考酮的产品,羟考酮是德国科学家在1916年开发的阿片类物质。
羟考酮生产成本较低,已经被用于其他药物,比如羟考酮和阿司匹林混合的复方羟考酮Percodan,以及羟考酮与泰诺酚混合的对乙酰氨基酚Percocet。普渡开发出一种纯的羟考酮药丸,具有与MS Contin相似的释放配方。该公司决定生产低至10毫克的小剂量药丸,而剂量为80毫克和160毫克药丸的效力远远超过市售的任何处方阿片类药物。正如巴里·梅尔(Barry Meier)在《疼痛杀手》中写道,“在麻醉的功效方面,OxyContin绝对是一种核武器。”
在向市场推出OxyContin之前,普渡与医生进行了重点论证,推断可能阻止广泛使用该药物的“最大负面”就是关于阿片样物质的“滥用”的担忧。但是,随着公司研发的OxyContin逐步成熟,一些医生开始争辩说美国医学界应该对“滥用“阿片类药物的偏见进行纠正。甚至于一些著名医生,如纽约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罗素·波特纳诺(Russell Portenoy)也曾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慢性疼痛未经治疗引发的各类问题,以及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的好处。“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显示这些药物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几乎没有副作用,”波特纳诺在1993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如是表示,将阿片样物质描述为“自然的馈赠”,他说偏见需要被消除。波多纳诺获得了普渡的资助,谴责了临床医生对治疗慢性疼痛麻醉药物的陈默和排斥,声称这是“阿片类恐惧症”的表现,并表示关于成瘾和滥用的担忧是“医学笑话”。1997年,美国疼痛医学院和美国疼痛学会都发表了关于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声明。该声明由有偿演讲者J. David Haddox博士主持的委员会撰写,而Haddox博士同样获得了普渡的资助。
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为OxyContin的一鸣惊人孜孜不倦地努力,他告诉同事自己对药物的成功感到非常欣慰。F.D.A.于1995年批准OxyContin上市,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疼痛。但普渡没有进行任何关于药物成瘾性或滥用的临床研究。但是,F.D.A.却极不寻常地批准了OxyContin的药品包装,其中宣传该药物比其他竞争对手的止痛药更安全,因为药物中获得专利的延迟吸收机制“被认为可以减少滥用风险。”当时在F.D.A.工作的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表示自己“没有参与批准过程”。F.D.A.当时负责整个监督过程的审查员柯蒂斯·赖特(Curtis Wright)不久后就辞职。两年内,他就在普渡公司谋得了一份职位。
萨克勒家族的莫蒂默,雷蒙德和理查德发起的OxyContin营销堪称是历史上最大的药物营销活动之一,采用了由亚瑟率先推出的许多有说服力的方法。1999年加入普渡任OxyContin销售代表的Steven May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个正义的事情。”他曾经这样告诉自己:“有数百万人正在忍受痛苦,而我们有解决方案。“(May已经不在普渡工作)该公司组建了多达一千名销售代表的营销队伍,并以图表形式向他们展示OxyContin的优势。May在普渡总部参加了为期三周的培训班。在培训后的庆祝晚宴上,他就和理查德·萨克勒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被惊到了,”他回忆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花花公子造就了这一切’,他有一家家族企业。我有一天想成为他。“
销售活动的主要目的是,OxyContin不仅应该被用于与手术或癌症相关的严重短期疼痛,而且还可以应用于不太紧急,持续时间更长的疼痛:关节炎,背部疼痛,运动损伤,纤维肌痛。OxyContin可以治疗的疼痛似乎无限。根据内部文件,普渡管理层发现许多医生错误地认为羟考酮的效力不如吗啡,这是被公司利用的误解。
1995年在给推广团队的一份备忘录强调,该公司“不愿意日”OxyContin只是为了癌症疼痛的治疗。普渡2002年预算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扩大”OxyContin在治疗疼痛方面的使用范围。就像May所说的那样,“有一点普渡做得很好,其游说的目标不仅是疼痛专家,还有全科医生。”在其内部文献中,普渡同样提到了接触那些“阿片类不耐受的患者”,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告诉我因为OxyContin是如此强大,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对这种可能存在成瘾性的药物,“目标应该是将最少量的药物销给尽可能少的患者。”但这种方法与制药公司的竞争要求不相符,所以普渡的做法恰恰相反。
May告诉我,销售代表接受了如何让临床医生“消除异议”的培训。如果一名医生询问有关成瘾性的问题,May会有一个准备好的谈话要点。他会说:“药物分发系统会减少毒品滥用的可能性。”他笑了笑,“这些都是具体的说辞。过了这么多年,我依旧记得,“他继续说,”很快我发现这是不正确的。“2002年,普渡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William Gergely告诉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州立调查员,普渡管理人员“告诉我们要说实际上是‘不会上瘾’”。
May并没有简单向医生重复OxyContin的推广语言;他向他们介绍了其他医生提供的研究报告和文献。普渡设立有一个负责游说的部门,并资助数千名临床医生参加各种医疗会议,就药物的优点进行介绍。在博卡拉顿(Boca Raton)等地,医生被资助参加疼痛管理研讨会。这样的投资非常有效:普渡公司的内部记录表明,1996年参加这些研讨会的医生开出的OxyContin处方是其他医生的两倍以上。该公司在医学期刊上发布广告,赞助介绍慢性疼痛的相关网站,并向公众分包含OxyContin信息的各种小玩意:钓鱼帽,毛绒玩具,行李标签。普渡还制作了患者满意的宣传片,就像一名建筑工人谈到了OxyContin如何缓解他的慢性腰痛,让他重返工作岗位。这些视频中还包括疼痛专家的推荐,被送到成千上万的医生那里。OxyContin的营销依赖于一个实证的逻辑圆:该公司用于说服医生的药物安全性结论恰恰是出自公司资助的医生之手。
多伦多大学临床药理学与毒理学系David Juurlink先生告诉我,OxyContin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医生倾向于相信阿片类药物的治疗效果。他说:“医疗实践的主要目标是缓解痛苦,医生看到的最常见痛苦之一就是疼痛。你有一个痛苦的病人,你有一个真正想要提供帮助的医生,现在突然间,你有一个解决方案,而且被告知这是安全和有效的。”
担任政府药物政策顾问的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基思·汉弗莱斯(Keith Humphreys)说:“这是真正的希腊式悲剧,那么多好心的医生被选中了。影响力令人难以置信。普渡大学资助医学再教育,资助医疗委员会,资助基层组织。“根据培训材料,普渡要求销售代表向医生保证,重复且无证据,”不到1%”的患者服用OxyContin成瘾.(1999年,普渡资助的一项使用OxyContin治疗患者头痛的研究发现,成瘾率为13%。)
在OxyContin推向市场的五年内,每年都能获得十亿美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销量放缓,”理查德·萨克勒在2000年告诉一个公司的销售代表团队。销售人员也在大力推销这种药物。在一份备忘录中,田纳西州的销售经理写道:“这是最近的红利时代!”分配到弗吉尼亚州地区的May惊讶地发现,很多业务熟练的同事能够获得数十万美元的佣金。进入公司一年来,May的销售情况非常乐观,普渡奖励了一次夏威夷旅行。随着处方数量的增加,普渡高管和公司董事会的萨克勒家族成员似乎很高兴为这种情况提供资金。内部预算计划将公司的销售队伍描述为“最有价值的资源”.2001年,普度制药公司支付了四千万美元的奖金。
有一天,May和有一位同事驱车前往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市。他们到那里拜访一位已经开出最高处方量的医生。当他们到达时,医生脸色发白。她解释说,自己的一位亲戚刚刚去世,那个女孩使用OxyContin过度。
亚瑟和莫蒂默萨克勒都经历了三次婚姻,雷蒙有一次婚姻。第二代萨克勒家族有15人,其中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孩子。萨克勒家族有着各种产业和相关利益。2011年,莫蒂默的遗孀,普渡董事会成员泰丽莎被授予威尔斯王子奖艺术慈善奖章。当颁发奖牌时,萨克勒家族所资助的德威图画廊负责人伊恩·德贾尔丁(Ian Dejardin)表示:“很难否认她的声音完全是圣洁的”。特丽莎的女儿苏菲已经与英格兰板球运动员杰米·达尔里姆勒(Jamie Dalrymple)完婚,其位于伦敦的房产价值4000万美元。雷蒙德37岁的孙子大卫·萨克勒(David Sackler)经营着一个家庭投资基金,是普渡董事会唯一的第三代成员。普渡私有化的事实是萨克勒家族与OxyContin关系仍然模糊的主要原因之一。上市公司会定期向股东披露相关信息。但正如巴里·梅耶(Barry Meier)所写:普渡是“萨克勒家族的私人领地”。
有时候,关注OxyContin的新闻记者会提及从药物销售流向萨克勒家族的利润,但这些故事往往将萨克勒家族描绘成一个涉足很多产业的庞然大物。然而,与任何大家族一样,内部也有不和谐的裂痕。80年代,莫蒂默起诉了他的前妻Gertraud,声称她非法占有了自己在第五大道拥有的公寓,并将其借给了模特儿和摄影师。普渡公司董事会里没有一个亚瑟的后代。在长岛的法院中存放着关于萨克勒家庭争夺亚瑟财富的文件,我发现一份文件表明,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亚瑟的遗产中“普渡股份”卖给了雷蒙德和莫蒂默。
“我没有普渡的任何股份,”的布鲁克林歌手、作曲家,亚瑟·萨克勒的孙子迈克尔·萨克勒-伯纳(Michael Sackler-Bern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亚瑟·萨克勒(Arthur M. Sackler)的后代与OxyContin的销售没有任何关系或从中受益。”萨克勒-伯纳没有提到Librium,Valium或MSContin等药物,但他补充说:“鉴于目前在OxyContin周围产生的争议,我感谢你澄清的事情。“
尽管莫蒂默·萨克勒(Mortimer Sackler)拥有普渡的大量股份,但他只是偶尔在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总部工作。1974年,据传是因为税收方面的原因,他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在欧洲享受这奢华的生活,不断往返于英国的豪宅,瑞士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比昂角。(1999年,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他荣誉骑士的称号,以表彰他的慈善事业。)但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雷蒙德·萨克勒(Raymond Sackler)却性情温和,总是喜欢每天到他在普渡的办公室工作,在那里他被称为雷蒙德博士。亚瑟的前广告同事约翰·卡利尔(John Kallir)回忆说:“雷安静,坦率,只有一次婚姻。他是三兄弟中最没有情调的。“
在OxyContin上市之后,有迹象表明像缅因州和阿巴拉契亚这样的农村地区存在药物滥用的情况。如果你将药片磨碎,吸食药物,或将它们溶解在液体中并注射,完全可以超越药物释放机制,一次性获得巨大的麻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阅读每个处方附带的警告标签来了解这些方法,其中明确指出:“使用破碎,咀嚼或粉碎的OxyContin片剂可能导致有毒剂量的快速释放和吸收”。随着越来越多的医生针对更多疼痛症状使用OxyContin,有些病人开始在黑市上卖药,街头价格是一美元一毫克。那些容易被病人操纵的医生,或是容易被金钱控制的医生会开出更多的OxyContin处方。
然而,该公司并没有将药物下架,或者承认它有一定的成瘾性。相反,普渡坚持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吸毒成瘾者并没有按照医嘱服用OxyContin。斯坦福大学教授Keith Humphreys说:“他们的说辞一直是一些垃圾人毁了他们的产品,”而2001年,普渡执行副总裁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在召开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这听证会的目的是找出阿片类药物滥用不断增长的缘由。他坚持认为OxyContin的营销是“以任何标准看都是保守的。几乎所有这些报告所涉及到的都是滥用药物的人,而不是具有合法医疗需求的患者。”
2002年,来自新泽西州吉尔·斯科列克的一名29岁女子吉尔·斯科列克(Jill Skolek)因为背部疼痛服用OxyContin。在服用药物四个月的某天晚上,她在睡眠中呼吸停止,最终死亡,只留下一名六岁的儿子。她的母亲玛丽安·斯科列克佩雷斯(Marianne Skolek Perez)是一名护士。此事令人她感到不安和迷惑,她确信OxyContin是危险的。佩雷斯写信给F.D.A.官员,敦促他们在OxyContin包装上添加关于成瘾风险的警告。
第二年,佩雷斯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以成瘾性为主题的会议。一个名叫罗宾·霍根(Robin Hogen)的沙色发男子,穿着针织条纹的西装和领结,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他是普渡的公关专家,并针对捍卫药物的合理性发起了一场有力的运动,警告报纸要小心他们的报道。“我们要去看他们说什么,”他答应了。他还拉上了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和他的副手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Kerik),以预防来自政府的打击。霍根曾经说过:“我们必须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来赢得这一天。”在哥伦比亚的活动中,他被问及佩雷斯女儿的悲剧。他警告说,不要这个悲剧中解读出普渡应承担任何责任。他说真正的问题是吉尔·斯科列克(Jill Skolek):“我们认为她滥用毒品”(在从普渡离职后,霍根对此表示歉意)。
另一位发言人是普渡的高级医疗顾问J.戴维哈多克斯(J. David Haddox),他坚持认为OxyContin没有成瘾性。他曾经把这种药比喻成一种蔬菜,说:“如果我给你一根芹菜,你吃了,那就会健康。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搅拌器里,试图把它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那肯定不会很好。“当哈多克斯走出会场的时候,佩雷斯撞到他身上。哈多克斯向后倒入一排折叠椅。佩雷斯回忆说:“这是柯达时刻之一。这可能是错的。但我喜欢它。“
亚瑟·萨克勒曾经写道:“所有的健康问题都该归因于个人”,而普渡的观点是,OxyContin过量是个人责任的问题,而不是药物有成瘾性。除了霍根和哈多克斯这样的人士,公司高管中包括法律顾问Howard Udell也在为药品站台。处理其事务的律师指出,Udell“就像《教父》中的汤姆·哈根一样,非常忠于萨克勒家族。”然而,Udell清楚地知道OxyContin的滥用效力。根据法庭文件,他自己的秘书沉迷于药物,随后被普渡解雇。
2003年,药品执行管理局发现,普渡的“侵略性方法”已经使OxyContin这种药物的滥用加剧。“药品执行管理局高级官员Rogelio Guevara得出结论,普渡”故意将药物相关危险性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公司继续把责任转移到吸毒者身上,甚至于向公众宣传一些成瘾青少年偷翻了父母的药柜。
在电话采访中,霍根告诉我,对于普渡和萨克勒,“有一种背叛的感觉——人们怎么可以通过滥用这种产品获得愉悦性呢?”霍根说公司收到了很多疼痛患者的来信,感谢普渡给予他们新生活。霍根强调:“今天,药物成瘾被视为一种疾病。”但那时不是。在过去十五年中我认为我们对成瘾性的理解大大增加。“
我回应说,几千年来人们都知道,鸦片衍生物是能够上瘾的。
“你真的需要和临床医生进行沟通,”霍根回答。“我不是医生。”
戴维·哈多克斯(J. David Haddox)是一名医生。2001年,他告诉美联社记者:“很多患者这样说,‘我正在服从医生给我开的药’,然后他们开始吃得越来越多了。”他补充说,“我没发现这是我的问题。”(哈多克斯目前仍在普渡工作,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事实是,OxyContin的危险性是药物固有的,而普渡也明白这一点。药物的缓释机制意味着,原则上患者每十二个小时服用一次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在夜间睡觉,这是常规止痛药(如吗啡等)的重要改善,不再需要更频繁的给药。普渡最初的广告之一就是两张小剂量杯的对比照片,一张标有“上午八点”,另一张“晚上八点”,还有一行字“记住,只需服用两次”,但是普渡的内部文件显示,即使在公司收到FDA批准之前,它就已经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服用OxyContin的患者都会严格遵守12小时的间隔。《洛杉矶时报》最近的一次爆料显示,在普渡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首例使用OxyContin的患者是波多黎各术后恢复的90名妇女。大约一半的妇女在十二小时之前就需要更多的药物。这项研究从未发表。对于普渡来说,掩盖这种结果的商业目的是明确的:十二小时的止疼功效是一个宝贵的营销手段。但是,对于许多病人来说,只需8个小时就会服用药片。尽管普渡声称没有成瘾性,但许多遵医嘱的普通患者还是出现了戒断症状。2001年3月,一名普渡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主管,描述了关于患者戒断症状的内部数据,并想确定是否写出结果。但这样做只会增加当前的负面新闻,因此就是——“我不会写这个。”
开出OxyContin的医生开始报告患者不断出现戒断症状(瘙痒,恶心,发抖),并要求服用更多药物。哈多克斯有了答案。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创造了“伪成瘾”一词。普渡解释称,伪成瘾的症状似乎与成瘾相似,但是由于无法解释的痛苦引起的。小册子继续说,”误会这种现象可能导致临床医生给患者打上“瘾君子”的标签。一旦疼痛症状得到缓解,这种伪成瘾通常停,但疼痛缓解通常是因为阿片类药物剂量的增加。
“当你推广这些超量的阿片类药物时,类似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就会增多,”David Kessler说。“这几乎是线性增长的。”美国市场上OxyContin的销售业绩很快就超过了伟哥。药物滥用和成瘾随处可见。弗吉尼亚州的医药销售代表史蒂文·梅(Steven May)说,似乎与OxyContin有关的问题不断转移,“就像癌症一样”。
根据罗宾·霍根的说法,萨克勒家族的成员“对引以为豪的产品发生这样的事情一致感到震惊。”萨克勒姆与普渡并没有正常关系,霍根说:“这是一个活跃的家族和一个活跃的董事会。“1999年,理查德·萨克勒成为普渡总裁。然而,作为一家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他并没有公司在业务方面的压力,也不像哈多克斯这样的人士会为普渡公开站台。事实上,尽管萨克勒主导了OxyContin的推广,但他从来没有关于这种药物的记录采访。普渡前经济学顾问,成瘾性专家安得烈科罗德尼(Andrew Kolodny)表示“我在普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去过公司的各种场合,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就算他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识他。”
即使在确认OxyContin被广泛滥用之后,普渡也拒绝承认是自己带来的问题。公司领导人主要担心的是阻止过量服药可能会使真正疼痛的患者丧失获得药物的机会。“他们说,‘我们需要确保这些产品可用于患者,’“霍根指出,“这是他们唯一的重点。”根据史蒂文·梅(Steven May)的说法,销售人员被指示摆脱争议,忽视滥用报告,并“继续销售”。到2003年底,F.D.A.向普渡发了一封警告信,提示“在宣传正文中没有提及药物存在严重的潜在致命风险,严重夸大了OxyContin的安全性”。
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的副手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2000年4月,在获得一系列缅因州关于人们滥用药物的新闻报道之后,普渡就首先意识到了OxyContin的问题。但是,普渡并没有依托媒体来深入了解OxyContin的分发情况。多年来,它与一个知名公司保持合作关系,该公司由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创立,为客户提供关于个别医生处方习惯的细节信息。普渡的销售代表使用这些数据来确定哪些医生需要关注。
这些数据也可以用来追踪药物滥用的模式。科罗德尼说:“他们知道什么人在开处方。他们也知道医生何时会滥发药片。”在2001年的听证会上,宾夕法尼亚州议员詹姆斯·格林伍德(James Greenwood)问弗里德曼,如果可能,普渡是否会采取行动。相关数据显示,一个乡村医生都能开出数千个OxyContin处方。
弗里德曼回答说,普渡评估“医生处方是否合理”不在话下。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信息呢?”格林伍德在回答自己的问题时说:“看看你们的营销技巧是多么成功。”
格林伍德观察到,在最近一起涉及宾夕法尼亚州医生理查德·保利诺(Richard Paolino)的案子中,他肆意夸大了OxyContin药物的功效,当地一位药剂师提醒当局进行关注。“他看着这些数据说:”天哪,本萨拉姆有一个叫保利诺的人,他正在开出很多处方,“格林伍德说。“现在,他有这个数据,却吹起了口哨。你有数据,而你会做什么?”
普渡并没有提醒当局。像保利诺这样的临床医生正在违法,最后他被判处至少三十年监禁。但医生过高的收入也为公司带来了相应的巨额收入。据我所采访的四个人说,在普渡,这样的处方人员被赋予了拉斯维加斯赌场为赌徒惯用的名字:鲸鱼。
2001年7月,时任康涅狄格州总检察长的理查德·布卢门塔尔(Richard Blumenthal)致信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我对OxyContin引发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升级的滥用状况感到惊讶和担忧,”他这样说,引用过量的死亡,成瘾,药店抢劫以及中用于支付OxyContin药物的“医疗补助异常增长”。布卢门塔尔承认其他处方药也会被滥用。“但是OxyContin是不同的,”他写道,“它更强大,更容易上瘾,更销售范围更广,更会非法获取,传播更快。”他呼吁普渡对OxyContin的营销进行“修正和改革”。
萨克勒无视他的建议,因此2004年布卢门塔尔代表康乃迪克州向普渡发起了一项投诉。它引用相关数据,表明五分之一的OxyContin处方患者给药间隔短于十二个小时。事实上,布卢门塔尔获得了普渡记录,表明公司官员在1998年就知道很多处方的给药时间是8小时甚至更短。在一份文件中,普渡的一名雇员称这个数字“非常吓人”。
相比于对公共卫生的关注,普渡考虑更多的是公司利润,因此并未对此类情况进行告警提示。如果OxyContin给药间隔普遍短于十二个小时的情况传播开来,那么该公司可能会因为此而失去所宣称的“每天两丸”市场优势,而保险公司可能会开始拒绝支付费用。早在1997年,一些福利计划已经将滥用OxyContin作为不理陪的借口。在1997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敦促同事们反对这种阻力,警告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成瘾性”可能是说“不”的一个简便方式。
自从OxyContin上市以来,普渡已经被投诉了数千次。2002年,霍华德·乌德尔(Howard Udell)表示,该公司将完全自行辩护。纽约的一名律师Paul Hanly发起诉讼,获得了5000名患者的委托签名,他们说在接受医生的处方后,会对OxyContin上瘾。在调查的过程中,Hanly获得了数千份文件。他说:“这些文件证实该公司已经开始在整个医疗界实施欺诈行为。有关药物的安全性声明都是营销部门发出的,而非科学部门的声明。这非常令人震惊,他们只是把这个东西推向了市场。“
2006年,Purdue与Hanly的委托者达成和解协议,赔偿7500万美元。不久之后,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联邦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一桩案件中,承认公司在销售OxyContin的过程中“意图欺骗或误导”,执行副总裁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霍华德·乌德尔(Howard Udell)和该公司的首席医疗官保罗·金海姆(Paul Goldenheim)承认犯下刑事轻罪。
玛丽安·佩雷斯(Marianne Perez)在弗吉尼亚州出庭作证。“我非常高兴,”她回忆说。她一直在与检方进行合作,并竭尽全力向公众通报OxyContin的危险。在判刑之前,佩雷斯发表了患者受影响的报告。“我想知道为什么萨克勒兄弟没有被追究责任,”她说。
佩雷斯在休庭期间看了看弗里德曼,金海姆和乌德尔,并告诉自己:“我体重有九十八磅,可以打倒一个人,”这一次她管住了自己。相反,她告诉他们,“你是邪恶的,混蛋。“高管们脸红了,但什么也没说。他们都接受了缓刑出发,并支付近3500万美元的罚款。普渡另外同意再支付六亿美元罚款。由于萨克勒家族和普渡从OxyContin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一些观察家认为该公司很快就会支付罚款。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Arlen Spectre表示,这种罚款是“犯罪行为的许可证”。
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曾为《医学论坛报》撰写了一个常规专栏,其中一个定论是烟草公司的不道德行为。1979年,他对香烟包装上的“狡猾警告”认定提示性不足,认为“对健康的危害应该更具体”。他还谴责报纸和杂志接受“误导”广告宣传,并认为出版社必须“以自己的良心为我们国家的死亡率做出贡献”。
1998年,已被数十个国家起诉的烟草业达成历史上最大的民事诉讼和解,同意支付246亿美元。烟草和阿片类药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F.D.A.批准的OxyContin是一种药物,而对于烟草来说,即使按指导使用也会可以杀死你,普渡认为不能把OxyContin等同于烟草。正如在烟草诉讼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密西西比总检察长迈克·摩尔(Mike Moore)指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烟草公司比普渡的钱更多。“要解决阿片类问题,你将需要数十亿,”他说,“单单治疗费用就可以达到五十亿美元以上。而且你还需要预防和教育开支。“
摩尔现在正在与保罗·汉尼(Paul Hanly)等其他律师合作,针对普渡和其他制药公司发起新的诉讼。十个州已经提起诉讼,私人律师正在与数十个市县合作,为他人提供服务。许多公职人员对强力止痛药的制造者感到愤怒。关于OxyContin的处方昂贵,纳税人经常通过医疗补助计划来支付账单。而且随着鸦片成瘾这种毁灭性后果的不断出现,公共资金必须为紧急服务或者戒毒治疗等公共服务买单。摩尔认为,萨克勒家族作为始作俑者,使这一事件的主要受益者,应该被公开指责。“我不称之为普渡,我称之为萨克勒公司,“他说。“他们是主要的罪魁祸首。他们欺骗了药品监管局,说它的效果能够持续12个小时。他们骗了成瘾者的财产。他们做了这一切,以拓展阿片类药物市场,使这个市场变成一锅舒服的温水。然后,其他一些公司看到水是温暖的,他们说:“好的,我们也可以跳进去。”烟草公司和阿片样生产者之间可能有重大的法律差异,但是摩尔道德上的平行是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是通过杀人来谋取利益。”
2015年8月的一天,一架飞机降落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走出机场,被律师包围着。八年前,肯塔基州起诉普渡,认为公司采取了欺骗性的营销手段。当时的总检察长格雷格·斯坦博(Greg Stumbo)发起诉讼;他表弟的儿子死于OxyContin过量。普渡用惯例来应对这一诉讼,力求将诉讼移交到其他地方,理由是该公司无法在肯塔基州派克县得到公正的审讯为了支持这项议案,该公司委托派克县进行人口统计学研究,并将其提交给法院,作为对陪审团存在潜在偏见的说明。这份报告透露了普渡可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根据调查,该县99%的居民表示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知道有人因使用OxyContin而死亡。十名受访者中有七名将OxyContin对社区的影响描述为“毁灭性”。
法官裁定普渡不能更换审判地,所以理查德·萨克勒不得不飞到路易斯维尔。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四名律师质疑他在OxyContin研发和营销方面的作用。首席律师泰勒·汤普森(Tyler Thompson)告诉我,萨克勒在会议期间的举止让他想起了杰里米·菲尔斯(Jeremy Irons)于1990年上映的传记电影《财富逆转》,萨克勒像极了其中被控谋杀妻子的贵族克劳斯·冯·布洛(Claus vonBülow),“脸带假笑和绝对缺乏悔意的态度。这让我想起了很多矿山公司来到这里,挖得一片狼藉,然后说道:‘这不是我的后院,所以我不在乎。’当时的肯塔基总检察长办公室诉讼人Mitchel Denham也出庭作证。“这是离奇的,”他回忆说,“我们与开发阿片样药物的公司所有人面对面质证。”Denham告诉我,在即将审判时,他发现了一张1997年派克维尔中学橄榄球队的照片。他说:“近一半的球员因过量使用药物而死亡。“这将会达到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
但是,Denham从未将照片提交给陪审团,因为在案件在审判之前,Purdue已经达成了24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这是萨克勒的决定。这个价格远超过普渡原来提供的报价—50万美元,但仍然不符合派克县的需求。普渡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在公开和解的情况下,公司会将有关内部文件进行封存。普渡有时声称从来没有与OxyContin有关的案件,但更确切地说,该公司从未允许案件进入审判阶段,通常是达成和解协议。而萨克勒家族“是这些人不被审判的主要原因,”Denham指出,“因为所有这些文件最终都可能在公共记录中。”肯塔基检察官被要求销毁数以百万计的文件,或者将其退还给普渡。医疗新闻网站STAT随后起诉理查德·萨克勒对内部文件进行封存。一位州法官赞成这一点,但普渡拒绝。迈克·摩尔(Mike Moore)指出:“他们努力隐匿的举动应该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
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于2003年辞去了普渡总裁的职务,但依旧是公司董事会主席。在洛克菲勒大学担任遗传学兼职教授多年后,他于2013年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他住在城市郊区的一个现代化山顶大厦中,身处科技企业家所梦寐以求的地方。根据他个人基金会的税收披露,他继续向耶鲁大学捐款,但他在2015年捐赠款项最多的一次是向新保守主义思想库“民主的民主国家基金会”赠送十万美元。我联系了萨克勒家族的十几个成员,但他们都拒绝回答关于OxyContin的问题。伦敦媒体顾问乔·谢尔顿(Jo Sheldon)打电话给我,并表示她与萨克拉家族的一些成员仍有合作。当我告诉她我对萨克勒家族有疑问时,她说我的疑问最好是指向普渡。谈到萨克勒家族时,她说:“其中一些家族成员还在参与普渡的事务,但是有些与此毫无关系,”当然资金往来除外。
鉴于萨克勒家族惯常所有的急躁情绪,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对于OxyContin的却一概保持了沉默。这些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有关他们财富污点的证据吗?他们是否只是简单地把它放在回忆里?“贪婪可以让人抵消负面行为,”安德鲁·科洛德尼(Andrew Kolodny)告诉我,有人认识莫蒂默,“我认为对他来说,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说:‘哇,我们真的很有钱。这很酷,我也不想对事情的另一面过多考虑。’“
律师保罗·汉里(Paul Hanly)指出,萨克勒家族坚决拒绝解决有关OxyContin的遗产问题可能是一种合法的策略,也是一个精明的策略。他说:“你所采访的越多,像我这样的律师和政府调查人员创造的目标就越多。”我想知道慈善事业是否是一些萨克勒家族成员赎罪的一种形式。但是,当考虑到该家族捐赠的广度时,一个领域显然缺乏:成瘾性治疗或任何可能用于对抗阿片样药物滥用的措施。
2010年8月,普渡(Purdue)用一种微妙不同的药物悄然取代了OxyContin。该公司已获得重新配制的OxyContin专利。如果你粉碎这些新的药丸,它们不再是一种细小的,可溶性粉末,而是一种不溶于水的胶状物质。F.D.A.批准普渡的新产品,但要在包装上强调安全性。F.D.A.已经批准了第一个这样的标签,其中包括关于该药物“滥用威慑”财产的索赔。
普渡大学的首席执行官Craig Landau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01年以后,普渡的研发部门主要致力于解决原有OxyContin产品的特定脆弱性。”常规看来,似乎OxyContin的制造者经过多年终于看到了他们方法的错误。但几乎可以肯定普渡考虑的是另一个因素:它需要阻止仿制药的竞争。亚瑟·萨克勒经常借助《医学论坛报》抨击仿制药。1985年,该报纸发表了一个故事,描述了在精神病科把品牌抗精神病药物更换为通用药物之后,一个老兵医院变得一团糟。(但根据《泰晤士报》的调查,FDA发现这个故事是假的,因为“通用药品”早在报道宣称的问题出现前六个月就被引进了”)。我曾经与一个专利律师进行了交流,其经常与仿制药制造商合作,据她所述她说,公司经常会在专利到期不久之前对品牌产品进行微调,以获得新的专利,并重新制定专有生产药物的时间。原有OxyContin的专利将于2013年到期。
变相承认药物不安全,研制出新药
普渡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原有的OxyContin容易被滥用。但是,在收到重新配制药物的专利后,该公司向F.D.A.提交了文件,要求该机构拒绝接受原始药物的通用版本,因为它们不安全。F.D.A.曾经有义务阻止普渡的任何低成本通用药品竞争。一年多来,普渡继续在加拿大出售OxyContin的原始配方。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OxyContin在安大略省温莎(毗邻美国底特律)的销量突然暴增四倍,这清楚地表明,这种药物正在流向美国黑市。通过I.M.S.的跟踪数据,普渡能够监测加拿大的激增,并推断其原因。(该公司承认,它意识到销售额的高峰,并指出已经提醒了当局,但拒绝透露是何时这样做的。)
在普渡重新开发OxyContin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于止痛药成瘾的全面蔓延之中。成瘾专家安德鲁·科洛德尼(Andrew Kolodny)告诉我,许多老年人仍然沉迷于重新配制的OxyContin,并通过处方继续获得药物。这些人合法购买毒品,按照指示吞下药片。“这是普渡的市场,”科洛德尼说。而年轻人想要开出处方并不容易,而OxyContin对他们来说也太贵,因此很多人转向黑市替代品,其中就包括海洛因。正如Sam Quinones在他的2015年出版的《梦幻之岛:关于美国阿片类物质疫情的真实故事》一书中详细介绍的,墨西哥的海洛因经销商会在美国各地对当地的药丸成瘾者提供毒品。这是OxyContin历史上一个可怕的悖论:原来的配方创造了沉迷于药丸的一代,强迫年轻的使用者戒断,但却让他们转而对海洛因上瘾。经济学家团队最近的一篇文章称,自2010年以来,海洛因成瘾因药物过度使用而急剧上升,标题为《OxyContin如何改变了海洛因的成瘾性》。一项调查显示,244人进入OxyContin戒断治疗后有三分之一转向其他药物。而其中有70%转而使用海洛因。
奎因诺斯调查中最令人惊讶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所发现墨西哥的海洛因贩卖者商业意识很强,这些所谓的哈利克斯群岛男孩和普渡的光营销策略相似。当哈利克斯群岛男孩们到达一个新市镇时,他们会通过当地的美沙酮诊所来确定他们的市场。而普渡则使用I.M.S.数据,定位对其产品敏感的类似目标人群。肯塔基州律师Mitchel Denham告诉我,普渡指出,“那些贫困,缺乏教育和机会的社区”都是其潜在的目标客户。公司还补充说,“因为工伤等原因,他们去看医生的次数更为频繁,对于疼痛治疗更有需求。“同样,哈利克斯群岛男孩会向潜在客户免费提供他们产品的样品。而普渡最初上市OxyContin时,该公司创建了一个计划,鼓励医生向患者发放免费处方的优惠券。在普渡停止该计划的四年后,已经赎回了34000张优惠券。
普渡现在承认有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危机,但认为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行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赞助一些州的“处方监测”计划到承担药物滥用教育方面的开支。首席执行官Craig Landau告诉我:“如果将对严重疼痛患者安全有效、且任何滥用风险的止疼药比喻成圣杯的话,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他补充说,该公司已经在致力于开发“非阿片类止痛产品”。普度特别强调,目前市场上还有许多种其他强大的止痛药,而且OxyContin在阿片类药物市场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2%。当然,单单从处方数方面看,这种说辞没有问题。但需要明确的是,大多数止痛药的处方周期非常之短,例如仅仅在手术后恢复期使用,而且剂量相对较小,但OxyContin的销售主要是由长期高剂量的处方推动的。如果按实际销售的药量衡量市场份额,OxyContin将会相当之高。一些医生估计可能高达30%。
美国占据了阿片类止痛药全球市场的约三分之一。但是,随着政治家和记者对成瘾性危机的警惕日渐提高,许多美国医生对待这些药物更加谨慎。普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即使是根据FDA批准的标签说明来服用OxyContin,患者也可能会发生身体依赖。“该公司认为身体依赖与药物成瘾有所不同,但阿片类药物处方医师协会(Physicians for Responsible Opioid Prescribing)医师Jane Ballantyne表示,对于患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区别: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停止服用药物,因为害怕停药后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瘾”。连锁药店CVS已经被指控从阿片类药物中获利,最近宣布计划将有关强效止疼剂的处方限制在一周以内,这一变化可能对滥用药物产生重大影响。也可能OxyContin已经达到市场饱和。近年来,美国临床医生每年大约开出2.5亿张阿片类药物处方。去年,在药物滥用较为严重的俄亥俄州,230万人,大约相当于该州人口的五分之一,接受了阿片类药物的处方。2012年,密尔沃基杂志《哨兵报》(Journal Sentinel)发表了一篇关于疼痛患者的故事,他们曾在普渡的宣传视频中提供了关于OxyContin奇迹的见证。在视频中谈到OxyContin疗效的施工人员约翰尼·沙利文(Johnny Sullivan)缓解了腰痛,但却对药物成瘾。2008年,当他在狩猎之旅中开车回家时昏了过去,他弄翻了自己的卡车,当场死亡。在普渡的小册子中援引沙利文的话说,OxyContin药丸“不是让我陷入昏昏欲睡,就是让我感到痛不欲生”。
多伦多医生David Juurlink告诉我,即使是那些克制成瘾性的用户,阿片样物质也是有问题的。他说:“阿片类药物真的能起到缓解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药效往往会逐渐减少。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增加剂量的原因。他们不得不通过加量来缓解疼痛。我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坚信自己是“合法”疼痛患者。他们服用了大量的阿片类药物,他们告诉我,他们需要这种药物,这显然是对他们造成了伤害。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药物一旦使用就无法减量。
普渡资助的鲁瑟尔波特内诺(Russell Portenoy)博士曾经主张可以长期广泛使用阿片类药物,但现在已经对他的观点进行重新评估。“是否我所谓疼痛管理,特别是关于阿片样物质治疗的方式,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他在2012年对《华尔街日报》说,“我想我是的。”(在一份声明中,波特内诺告诉我,他“重新调整了痛苦管理方法,并补充说:‘没有资助者对我的想法产生不当影响’”)
在辩护层面,波特内诺指出,在二十年前,医生们还没有掌握目前有关阿片类药物和成瘾的知识。萨克勒家族和普度制药公司可能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为造成灾难的角色道歉,因为整个90年代,他们都依赖于普渡做出的关于OxyContin安全性的一系列错误假设。但是,普渡对任何可能限制OxyContin使用的措施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面对可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止痛药处方的措施,普渡及其各种盟友往往对此反应巨大,一再称这不符合疼痛患者使用OxyContin的利益。华盛顿大学精神科医生马克·沙利文(Puri Dave)一语中的:“我们的产品并不危险,但是人太过危险。”
去年,曾于2011年正式宣布阿片类药物滥用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了第一套指南,以帮助减少如OxyContin等强效止痛药的处方。该指南说:“阿片类药物不应被视为慢性疼痛的常规治疗方法,建议医生首先考虑物理治疗等”非药物“治疗方法,或者选择”非阿片类药物治疗“。
普渡和其他制药公司长期资助那些常常为疼痛患者治疗发声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并不具约束力,而许多非营利性组织为防止被解散而会抵制指导方针。这种障碍在国家和州的层面都是典型的存在。美联社和公共诚信中心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报告显示,普渡高管认罪后的2007年曾组织了一批游说队伍,打击任何可能侵害其业务的立法行动。在2006年至2015年期间,普渡和其他止痛药生产商及其相关非营利组织花费了近9亿美元用于游说和政治捐款,这是同期枪支游说开支的八倍。
由于普渡(Purdue)使得OxyContin药丸研碎成粉无用,因此处方数量已经下降了40%。这表明此前近一半的原药消费者可能已经把它研碎了。正如David Juurlink对我所说的那样,将药物再造称为“滥用的有效威慑”并不恰当,就像瓶身上所指示的那样,止痛药仍然可以成瘾者滥用。但是,普渡市面临市场的萎缩和竞争的不断加剧,并没有放弃对新用户市场的开发。2015年8月,F.D.A.批准将OxyContin的应用拓展到十一岁的儿童,遭到了各界的大量批评。
福布斯估计,萨克勒每年从家族企业的收益约为七亿美元,而正如萨克勒家族肯定会想到的那样,OxyContin的实际未来可能是全球性的。许多大公司其销售额一旦在美国达到峰顶,就会将目光转向国外。在美国上市OxyContin之后,普渡将第二战场搬到了加拿大和英国。在多伦多大学,该公司赞助了一个关于医学和牙科学生疼痛管理的课程。讲师是普渡发言人的成员。学生会收到了普渡编发的免费教科书,将羟考酮描述为“中度”阿片样物质。在受到学生和医生的广泛批评后,该课程已经停止了;其中一个评论家是大学医生瑞克格莱则(Rick Glazier),他的儿子丹尼尔于2009年死于OxyContin过量。
由于OxyContin在美国境外的上市,其在美国的悲剧再次上演:药物的地理分布恰恰也是成瘾性,药物滥用以及就此引发的各类死亡事件盛行地区。但是,萨克勒家族依旧在国外加大对药品的推广力度,现在正在通过名为萌蒂(Mundipharma)的普渡关联公司将其药物推广到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普渡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是为OxyContin创造一个市场,通过对大量未经治疗的慢性疼痛患者作出大胆的声明来灌输认知需要。随着普渡进入对阿片类药物有负面情绪的国家,其营销方式并没有改变。根据2016年《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就在萨克勒家族的OxyContin营销已被医疗机构驳回之后,萌蒂依旧委托相关学者进行研究,显示这些国家有数百万人患有慢性疼痛。该公司组织了一些人,并向医生支付酬劳来介绍OxyContin的优点。事实上,一些目前在国外也有为OxyContin鼓吹的医生,他们被称之为“疼痛大师”。
《泰晤士报》的报道描述了佛罗里达医生Joseph Pergolizzi,其经营一个疼痛治疗诊所,并宣传自己发明的止疼剂使用流程。他还在巴西等地就OxyContin的效果进行宣传。在墨西哥,萌蒂断言,80万人(约该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患有慢性疼痛。在2014年的采访中,萌蒂执行官拉曼·辛格(Raman Singh)表示:“新兴市场上每一位患者都应该能够获得我们的药品。”由于明显的原因,“阿片类恐惧症”这一说法在美国基本上被废除了。但萌蒂的高管仍然在国外使用它。
“这与烟草业的做法是一回事,”摩尔对我说。“他们在美国陷入困境,他们看到市场份额下滑,所以他们出口到比那些规定较少的国家或地区。”他补充说,“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会看到因此造成的很多死亡。“五月份,国会的几位成员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它协助阻止OxyContin的传播,并明确在其中提及了萨克勒家族。他们写道:“国际卫生界难得有机会看到未来。不要让普渡摆脱他们对无数美国家庭造成的悲剧,还要在别的地方找到新的市场和新的受害者。”前F.D.A.专员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认为,美国的阿片样药物的洗白是现代医学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我问及萌蒂在国外推销OxyContin的看法时,他说:“这让我恶心,感觉很不舒服。“
今年早些时候,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宣布,将对旗下的一所曾以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命名的寄宿制学院重新命名,因为卡尔霍恩“作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全国领导人,积极推动了奴隶制,这与耶鲁大学的使命和价值观相违背”。这一举措并非没有非议。当然,这一举动标志着耶鲁开始对历史上曾经获得崇拜的人进行反思,扪心自问其是否与当代的道德标准相符。在牛津,来自南非的罗德学者最近发起一项运动,撤走了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的雕像。
一然而,当代的萨克勒家族却逃脱了。其可疑的商业行为不是几个世纪以前的旧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如果现在的统计资料有任何迹象的话,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你可能会得知有6名美国人死于对阿片样药物的滥用。然而,耶鲁大学似乎并不急于对以雷蒙德Raymond和贝弗莉·赛克勒(Beverly Sackler)命名的生物,物理和工程科学研究所进行重新命名。
精神病学家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在谈及萨克勒家族时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完全被排除在关于因果关系的辩论之外。从过去几十年来看,一个真正的慈善家庭会说:‘你知道有几百万美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因为我们而上瘾,’而真正的慈善事业该是为了照顾他们而捐款。在这一点的基础上,这些人的名字被添加到建筑物中。但萨克勒家族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慈善事业。这只是萨克勒家族的荣耀。“根据美国成瘾医学协会的统计,有超过250万美国人患有阿片类药物失调。弗朗西斯继续说道:“如果萨克勒家族真正想要洗清他们的污名,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拿出很大一部分的财富,并创造一个为所有成瘾者提供免费治疗的机制。”炸弹发明家诺贝尔创建了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由约翰·洛克菲勒(John D.Lockefeller)的后代经营的几个慈善组织投入很多资源来应对气候变化,并批评曾创立的石油公司(现称为埃克森美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去年,瓦莱丽·洛克菲勒·韦恩(Valerie Rockefeller Wayne)告诉CBS:“由于家庭财富的来源是化石燃料,我们感到了更大的道德责任。”
前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迈克·摩尔(Mike Moore)认为,除非更多的公众意识到他们的财富来自于阿片类危机,否则萨克勒家族根本不会有这种姿态,直到。摩尔回顾了他与烟草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首次和解会议:“我们问他们,”你想要什么?“他们说,”我们想要去鸡尾酒会,没有人会来,问我们为什么杀人。这是一个明确的回复。”摩尔感到困惑的是,博物馆和大学能够继续从萨克勒家族手里收钱,没有任何问题或争议。他想知道,“如果被赞助的这些基金会,医学院校和医院开始说:‘有多少婴儿自出生就对阿片样物质成瘾,那会发生什么?“现在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个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孩子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有10%的新生儿依赖于阿片样物质。田纳西州东区的一名地区检察官最近代表婴儿瘾君子“Baby Doe”对普渡和其他公司提起了诉讼。
摩尔坚信,普渡高管将无法和解所有案件。“在某个地方,总会有一个陪审团,在某个地方,总会有一次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最大审片,”他说。Paul Hanly指出,最终的审判可能会让普渡申请破产。“但是即便他们这样做,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说,“我会开始仔细研究萨克勒家族的责任。”
前普渡公关部门负责人罗宾·霍根(Robin Hogen)表示:“我不想被描绘成为公共卫生危机的道歉者。但是我想明确的是你在跟一个曾经非常尊重萨克勒的人谈话。萨克勒家族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流的。“我问他对于很多医生和公共卫生机构官员认为萨克勒家族该对药物滥用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一事有何种看法。“我不是医生,”霍根反驳道,“我真的不能评论。”
萨克勒家族一直在营销的自信游戏中表现出色,令我震惊的是他们所汲取的最大的伎俩是将整个家庭从家族企业的历史中剥离开来。我想起亚瑟·萨克勒的名言——你应该努力让离开时的世界比你来到时更美好,我想知道萨克勒家族的行为道德准则。但是,整个家族拒绝置评。
我最近去了长岛的阿马甘谢特,遇见一个我称之为杰夫的男人。在一家餐厅,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与药瘾的斗争历程。十年前,当他还是青少年时就开始滥用阿片样物质。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他特别喜欢OxyContin,因为它能够带来“纯粹的兴奋感”。在吮吸完药丸的红色涂层后,他用点烟器的火焰将药粉碎,然后吸食。好在他并不注射药物。“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总是告诫自己,”我永远不会将针在我的胳膊上,“他说。
杰夫坦言,接下来的十年他一直在滥用止痛药,遇上一个女孩,相爱,并让她也对阿片样物质上瘾。有一天他的经销商缺药,但告诉他:“我会给你一袋海洛因,只有二十美元。”杰夫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屈服了。起初,他和他的女友只是吸食海洛因,最终他们开始注射药物。他们结婚时药瘾很大。杰夫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对阿片样物质成瘾的男孩。他说:“医生不得不用吗啡让孩子断奶。”
经过长时间的康复治疗,杰夫已经有一年多不再吸食阿片类药物。他的宝宝健康,妻子也戒断了。回想起来,他说,他觉得青春期一个冲动的决定就让他走上了不归路。“这就是关于这种药物的一切,”他说,“我刚刚经历了飓风般的过去。”
我们离开餐厅,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漫步,两旁是大房子。在最糟糕的岁月里,杰夫曾经是该地区的一名工匠。我曾要求他告诉我一个他提供过服务的房产,我们驻足在一个隐匿于密集灌木丛之后的别墅之外。那是莫蒂默·萨克勒(Mortimer Sackler)的房产,杰夫倍感讽刺。他说:“我不会告诉你有多少次我就来到这里,坐在一辆卡车上,吸食药丸。”
我们旁边是一扇装饰华丽的木门,门后是由有巨大垂柳的院子。当我欣赏这棵树时,杰夫说,对于那些打理草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关于屁股的痛苦”。他解释说,每当风起时,柳树枝条散落在草坪上。“但这个地方必须是完美的,”他说,“地上不能有一片叶子。”所以一个员工定期回来,清理了这个烂摊子。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