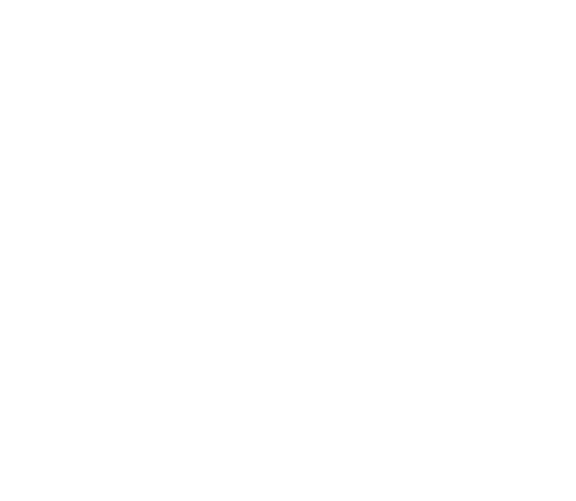人类和细菌间的军备竞赛:新型抗生素为何如此难寻
▲抗微生物肽穿过细菌细胞膜的模拟场景
▲利奈唑胺的分子模型,灰、白、蓝、红和青色圆球分别是碳、氢、氮、氧和氟原子。利奈唑胺是一种治疗耐药性细菌感染的合成抗生素。
据国外媒体报道,人类正处在与抗生素耐药性抗争的最前沿。一位86岁的慢性2型糖尿病患者因可怕的脚伤前往医院救治。由于长期没有接受治疗,他的脚部感染已经非常严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让人意外的是,广谱抗生素美罗培南(meropenem)和万古霉素(vancomycin)对此都完全没有效果,而在传统上,万古霉素被认为是“最后一线抗生素”,用于治疗其他抗生素都无效的严重感染。
医生们很清楚,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然而,即使有了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试验的结果依然令他们感到惊讶。这名男子脚上感染的不是一种细菌,而是三种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和鲁氏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lwoffii)。每一种细菌都具有对多种药物的耐药性。这家位于巴西的医院缺乏应对这一情况所需的资源。患者被转到更大的医院,但由于损伤过于严重,他不得不进行截肢。
这是一个报道于2012年的真实故事,是众多相似故事的缩影。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还有一位因心脏衰竭而死的57岁女士,罪魁祸首是耐青霉素的细菌。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内华达州的一家医院,一位女士在隔离室中不幸死亡,她所感染的细菌对医院中所有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
据估计,仅在美国每年就有两百万感染了具有耐药性的微生物,其中大约23000人死亡。在文明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知道如何杀死细菌;但为什么有了现代科技之后,人类依然对一些致命病菌束手无策?
抗生素的诞生
抗生素疗法的最初应用是在1867年,来自于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李斯特注意到,他的许多患者在接受手术之后都不得不截肢,或者很快死去。许多人将此归结于“瘴气”(miasmas,有毒的“糟糕”空气)或氧气对开放伤口的影响。
李斯特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一直在追踪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研究,后者的实验结果显示,食物的腐坏与氧气无关,而是因为一些微小的、肉眼看不到的生物。李斯特提出,这些生物同样也是造成他的病人出现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巴斯德为避免出现这些结果提供了三个选项:将这些生物过滤掉;把它们用高温煮死;或者用化学物质杀死它们。前两种方法可以立即排除,第三种方法则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作为一位充满好奇心且学问深厚的科学家,李斯特当时已经听说了矿物杂酚油(从煤焦油或其他矿物油中蒸馏而成的液体)在防止铁道枕木腐烂上的应用。出于同样这些微生物需要对患者痛苦负责的直觉,他决定尝试用一种煤焦油的馏分——碳酸——来治疗患者的伤口。最初的结果令人震惊:此前普遍需要截肢的复合骨折患者,现在竟然可以在肢体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康复。
李斯特所发现的其实是世界上第一种医用消毒药水,而非抗生素。碳酸对人体具有毒性,因此只能谨慎地用于处理伤口。成果丰富的德国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希望能做得更好。他对德国民间传说中神射手Freischütz的故事十分着迷,故事中百发百中的神射手与魔鬼达成交易,获得了6枚能避开所有障碍击中目标的神奇魔弹。那么,有没有可能制造出一种能杀死细菌,但不会伤害人类细胞的化学魔弹呢?
埃尔利希的学术背景是组织学,尤其擅长对组织样本染色,以便在显微镜下观察。他发现,某些染料分子会使一些细胞着色,对其他细胞却没有效果,就像传说中会寻找目标的神奇魔弹一样。埃尔利希意识到,这些染料分子或许能帮助他实现选择性抗生素的梦想。
1909年,埃尔利希的想法最终获得了成功,他和日本助手秦佐八郎发明了砷凡纳明(arsphenamine,又称作洒尔佛散、606)。这是一种有机砷染料,能够在不杀死病人的情况下杀死梅毒细菌。不过,砷凡纳明只对梅毒有效。德国法本公司(IG Farben,全称为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即“染料工业利益集团”)拜耳(Bayer)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始思考能否用同样的方法开发出用途更广的抗生素。化学家Josef Klarer和Fritz Miestzsch合成了数千种染料,并由德国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在实验室中对感染病菌的小鼠进行了试验。在无数次失败之后,一种称为百浪多息(prontosil)的染料终于获得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种真正通用的抗生素。
尽管拜耳实验室团队认为埃尔利希的理论是百浪多息药效显著的原因,但后来的研究显示,这与该化合物的染色能力并没有关系。
到底是什么让抗生素拥有如此神奇的功能呢?
相对而言,发明能在皮肤和组织表面上杀死微生物的新型消毒药水要简单得多。然而,消毒药水是非常可怕的杀菌剂:破坏细菌基本结构的化学物质往往也会破坏人体细胞中的相同结构。幸运的是,有些细菌结构并不会存在于人体细胞中,即使存在,它们也非常不同。这就是抗生素功能的关键:利用细菌与人类细胞相似而不相同的事实。
从第一种抗生素被发现以来的将近一个世纪时间里,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细菌特异性特征库。例如,抗生素磺胺(sulfanilamide)针对的是人类身上不存在的一部分细菌生命过程。叶酸和维生素B9一样,在所有生物体中都是DNA合成的必需物质。人类通过食用水果和蔬菜获得叶酸,但细菌必须通过与人体细胞完全不同的过程从头开始合成。与其他磺胺类药物一样,磺胺通过在细菌体内竞争酶反应位点,抑制叶酸的合成,从而阻止细菌的DNA合成过程,同时不会对人体新陈代谢产生影响。
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1928年偶然发现的青霉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β-内酰胺类抗生素(如美罗培南),针对的也是人类细胞不具有的部分细菌结构:细胞壁。细菌细胞就像是装得太满、用麻线包扎起来的烤肉,麻线就相当于细胞壁,一旦去掉,细菌细胞就会“爆炸”。
细菌构建细胞壁的过程很像人们建造篱笆。先放置一些栅栏柱,然后用钉枪将水平支撑木条和木板钉上去。青霉素的作用就是堵住细菌的“钉枪”,使其细胞壁中的“栅栏柱”无法连接起来。另一方面,万古霉素等糖肽类抗生素则会像厚厚的防弹毯一样,包裹住细菌细胞壁的栅栏柱,细菌的“钉枪”依然能使用,但没有一颗钉子能钉上去。
这些都是理想的情况。其他主要抗生素类别所针对的细菌生命部分与人类细胞中的机制更为相似,但依然存在足够的差异,使它们能成为作用目标。这些差异可以非常微小,但在作为选择性抗生素和消毒药水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条细小的界线。
举例来说,许多药物以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为目标。抗生素能阻止紧密缠绕的DNA被解包和读取,阻塞RNA转录过程,或者关闭将RNA分子转录、翻译为蛋白质的分子工厂。在这些情况下,人体细胞中的等同过程由不同形状的酶完成,并且不具有抗生素进行工作时所需的相同“抓手”——如果一样的话问题就严重了,这些过程的中止对人类细胞来说同样致命。
细菌的反击
这是人类与细菌斗争故事中的进攻部分,但还有防御的部分:细菌具有反击的倾向。一种简单的防御方法是在抗生素造成伤害之前将其清除,就像用水泵不断从地下室抽水,防止被水淹没一样。细菌的外排泵会不断清除抗生素,阻止它们进行工作。一个外排泵可以通过识别和去除几种不同类型的抗生素来提供多重耐药性,从而成为难以对付的耐药机制。
细菌还可以合成新的蛋白质,在抗生素发挥作用之前断开并解除其功能结构。这个策略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某些细菌产生的β-内酰胺酶,又称为盘尼西林酶(penicillinase)。这种新的酶唯一的功能便是打开具有弹性加载的β-内酰胺四元环核心,使其无法作用于细菌的细胞壁。这类蛋白质通常对一类抗生素具有高度特异性,不会对其他类型产生作用。我们用来对付这种耐药机制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原有的抗生素与针对新酶的新抗生素打包在一起。
细菌拥有的另一种防御策略是制造能与抗生素结合的蛋白质酶,作为分子“约束衣”,阻止它们抓住目标并使其成为无助的旁观者。这些酶的工作机制是利用磷酰基、乙酰基、核苷酸基、糖基或羟基等化学基团与抗生素的关键部分结合,阻止它们与细菌的目标部位结合。通常而言,这些酶只对某一抗生素家族起作用,因此交叉耐药性并不是问题。
对细菌来说,或许最明显和最有效的耐药方法是改变抗生素的目标,使抗生素无法识别出自己。这种耐药方法非常普遍,而且有许多实现的途径。例如,只需将细胞壁“栅栏柱”末端的氨基酸由D-丙氨酸变为D-乳酸,一个非常小的调整,就可以使万古霉素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完全失效。一旦目标改变,我们就无法再用原来的“魔弹”来摧毁它们。
原理上,对付这类耐药细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到新的“魔弹”。然而,许多抗生素来自微生物本身,生存压力会迫使微生物物种不断发展出击败竞争对手的武器。这些微生物制造抗生素的方式往往不是很灵活:它们非常擅长制造特异性的结构,但如果这一结构不再与目标相吻合,它们就很难调整过来。我们还在大自然中发现了许多显而易见的抗生素,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抗生素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广谱抗生素中,除了头孢洛林一种之外,其他都是在10年前发现的,几乎一半发现于1950年到1960年的“黄金时代”。
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方法是寻找隐性抗生素(cryptic antibiotics),这就涉及到促使细菌生成它们通常不会生成的分子。这种方法能否奏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目前我们的最佳选择是转向有机化学,该领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精确的工具,以其他学科难以想象的方式对分子进行调整。利奈唑胺(Linezolid)正是人类利用有机化学技术从无到有开发出来的一种抗生素,能阻止核糖体与mRNA连接,从而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我们还能用有机化学对自然界中发现的抗生素进行调整。例如,美国Tetraphase制药公司正在尝试改造四环霉素(tetracyclines),使其适应多种耐药性细菌的目标位置。
我们唯一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因为细菌永远不会放弃。制药业已经耗费了大量资金寻找新的抗生素,许多公司在一无所获之后宣布放弃。这很危险。我们需要明白,探索过程必将是缓慢而艰难的。尽管科学家在努力设计更好的有机化学工具,以更快地制造抗生素分子,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抗生素耐药性是一场人类一开始就处于下风的军备竞赛。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更多,否则等待我们的只有失败。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与此息息相关。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