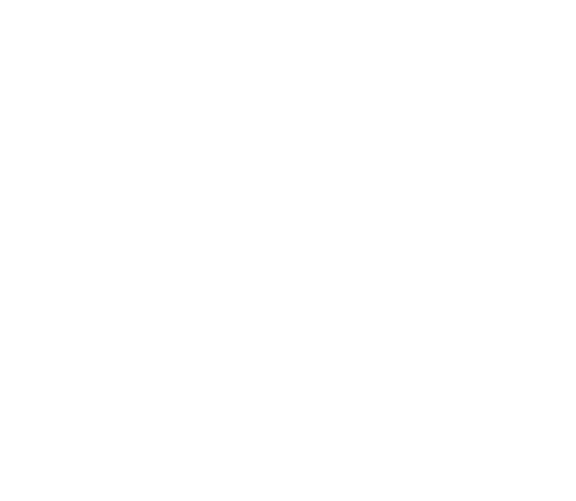超级细菌威胁全球,新型抗生素离我们还有多远?
据国外媒体报道,面对新出现的耐药超级细菌,坚定的科学家们正冒险深入地球深处寻找稀有和不寻常的细菌,而这些细菌可能是未来抗生素的希望。
2011年的一天,纳瓦尔特·奇普瑟姆(Naowarat Cheeptham)第一次冒险进入铁幕洞穴(Iron Curtain Cave),随即黑暗吞噬了一切。这位生物学家转过身去,离开了铁梯——这是返回头顶那一小块阳光的唯一途径——她强迫自己继续朝黑暗前进。
48岁的奇普瑟姆被她的朋友们亲密地称为Ann,并不是偶然发现了铁幕洞穴。这个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奇里瓦克山区的洞穴是由当地建筑承包商和业余洞穴爱好者罗伯·沃尔(Rob Wall)于1993年发现的。沃尔常常在山上探险,寻找未知的洞穴,甚至可能会为自己的探险乐趣而打开洞穴。加拿大这个地区的许多洞穴实际上都是封闭的天坑。因此,沃尔的搜寻工作涉及到一个被称为“挖掘”的过程,毫无疑问,沃尔正是通过挖掘对那些凹陷地面进行勘探。有一天,沃尔在穿过树林的途中突然掉进了一个洞里。第二天,他带着一个朋友和一把铲子回来了。两人挖了三个小时,挖出了一个10米深的洞,洞底有两个小房间。这就是沃尔一直在寻找的一切。
直到六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当沃尔向一群朋友炫耀他的发现时,他们中的一个人才注意到有一阵微风从洞后吹过。所有人进行了调查,搬开岩石,结果打开了一个通往半公里原始洞穴的入口。地下的空间里闪耀着石膏水晶,洞壁和地上满是石笋和钟乳石。从来没有人去过那里。“它很漂亮,”沃尔说。
2011年,奇普瑟姆联系到了沃尔。这位生物学家一直在寻找当地的洞穴进行探索,沃尔邀请她就奇利瓦克河流域洞穴(Chilliwack River Valley Cavers,CRVC)做一次演讲,并解释她的项目。奇普瑟姆解释说,黑暗潮湿的地下洞穴里充满了生命,它们大多是未知的极端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所处的环境从生物化学上讲对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形式都是不利的。对于奇普瑟姆和她来自汤普森里弗斯大学(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生物科学系的同事们来说,寻找这些极端微生物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是为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全球威胁之一——抗生素耐药性——而进行的最后一搏。
尽管极端微生物并不是寻找新抗生素的唯一途径。但是,由于这些微生物不仅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生存,而且能在其他细菌可能死亡的栖息地茁壮成长,这表明它们的化学分泌物特别有效。洞穴是研究稀有细菌的丰富源头,因为它们具有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并且与细菌通常生长的其他环境隔绝。
实际上,被用来制造抗生素并不是细菌本身,而是它们的代谢物,也就是它们在生长过程中而产生的化合物。例如,酵母的代谢产物是发酵的结果。人们曾经认为这些代谢物的存在是为了杀死竞争细菌。然而,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朱利安·戴维斯(Julian Davies)在内的许多生物学家都提出了一种新思路,认为这种代谢物在自然界中的真正功能可能是充当细菌之间的一种语言,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并共享资源。在洞穴里,这一点尤为重要。毕竟,正如奇普瑟姆所指出的那样,“(在洞穴栖息地),它们是竞争而死,还是共同合作生活下去更好?”
▲图示:奇普瑟姆被带领导铁幕洞穴入口处。
在看完奇普瑟姆的报告后,51岁的当地洞穴学家道格·斯托罗辛斯基(Doug Storozynski)自愿帮助她探索当地的洞穴。虽然不像附近其他洞穴那样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但铁幕洞穴仍然会让初次进入的人感到紧张,需要有经验丰富的向导来指引其前行。当他们下到黑暗中去的时候,起初奇普瑟姆感到幽闭和恐惧。但是,随着她和她的团队在狭窄的空间中爬行、穿过冰冷的地下水道和粗糙的岩壁时,这个洞穴变得生动起来。钟乳石悬挂在洞穴顶部,石笋从古老的地上升起。
细菌以石吸管次生矿物沉积物的形式存在于二次矿床中——这种天然的钙质沉积物也包括钟乳石和石笋。在黑暗中摸索了15分钟后,奇普瑟姆和她的团队来到了山洞的后壁,那里有一层红色的、像窗帘一样的灰泥堆积物,这就是洞穴名字的来源。在这堵墙的旁边,洞顶向下倾斜到侧凹的黑暗中。奇普瑟姆的目标是悬挂在洞顶上的60厘米长石笋。当蓝灰色的洞穴在眼前逐渐成形,奇普瑟姆的恐惧被好奇和兴奋所取代。
她爬到最佳的位置,跪在地面和石笋之间的狭小空间里,从背包里取出样品盒。她用无菌镊子从第一个石笋的顶端刮下一个极其细微的部分,把它放进一个50ml的试管里,然后把它固定住。她在头灯的照射下迅速工作,将石笋样品装满了自己所携带的六个试管。随后,探险队回撤到地面。奇普瑟姆将这些样本保存在“冷却袋”中,以保持细菌活性,以便于在她的实验室里进行分析。
在世界各地,从治疗常见感染到化疗的所有外科手术都依赖于抗生素。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大肠杆菌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我们赖以维持生命安全的药物都未能跟上这种感染传染病和病毒的快速进化。随着抗生素继续失去药效,我们甚至失去了治疗最基本疾病的能力。这种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将抗生素耐药性视为“当今全球健康、粮食安全和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这并不是一场新的危机。2014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要求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调查抗生素耐药性对经济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抗菌药物耐药性审查》(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报告指出,全球每年因耐药超级细菌导致的死亡人数为70万,到2050年估计每年死亡人数为1000万。奥尼尔还预测,如果该危机持续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响应,由此带来的全球人口将使得全球经济产出降低3.5%,相应经济损失约为100万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倍。然而四年过去了,我们离解决这个问题还很遥远。
截至2018年4月,一种新的伤寒菌株——对五种不同的抗生素具有耐药性——导致巴基斯坦的四人死亡,并影响岛800多人的身体健康。同样在今年,英国公共卫生部门报告了“史上最严重”的淋球菌感染病例,此前英国的感染病例从2008年的不到1.5万例飙升至2015年的4.1万例。即使是抗生素粘菌素——当所有其他抗生素都失效时,通常作为最终治疗手段使用——也正在失去效力。美国微生物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在2017年的一次峰会上报告说,拥有抗粘菌素mcr-1基因的细菌现在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2018年4月,为了应对这种可怕的判病结局,巴基斯坦阿加汗大学(Aga Khan University)病理学教授鲁米娜哈桑(Rumina Hasan)对《纽约时报》说,“抗生素耐药性是对所有现代医学的威胁——可怕的是,我们别无选择。”
与常见的误解相反,人类并没有因为过度接触产生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相反,细菌本身通过进化来应对我们杀死它们的各种方法。根据奇普瑟姆的数据,在任何时候我们体内都有大约1.3千克的细菌。它们的总质量大致相当于人脑的质量。不管家用厨房清洁剂和肥皂产品如何做宣传,但99.9%的细菌实际上是中性的,或者对我们的健康有益。
▲图示:奇普瑟姆在她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大学城的实验室研究细菌样本
“以前,我们认为过度使用和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奇普瑟姆解释说。“事实上是我们在训练细菌。当细菌看到三氯生(在清洁产品、肥皂和牙膏中发现的一种抗菌剂)向它们靠近时,它们想要像地球上所有生命一样活下去。大多数细菌会死亡,但有些会找到帮助他们生存下来的防御机制,比如在细胞壁中形成一个孔,让细菌释放药物的速度比药物侵入的速度更快。”她用手指轻敲着桌子,强调了这一点,显然她仍对其心存敬畏。“细菌比我们想象得要聪明。”
这并不是改变研究人员对细菌看法的唯一发现。“自1928年以来,我们就知道细菌可以进行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但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将后者(也被称为“水平基因转移”)和耐抗生素基因的传递联系起来,”奇普瑟姆解释说。
最典型的是,细菌通过无性繁殖产生后代,通过不断分裂产生基因组的精确拷贝(这种方式称为垂直基因转移)。在无性繁殖情况下,抗生素能够杀死有害细菌,因为抗生素每次处理的都是有害细菌的精确基因复制品。然而,在有性生殖过程中,基因在母细胞之间交换,而后代保留了这两组基因,创造了一个更复杂的有机体。这可能发生在一个物种内部,也可能发生在物种之间。例如,并非所有的大肠杆菌都是有害的。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大肠杆菌的毒株(如O157:H7或O104:H4)与沙门氏菌混合,从而生成出更致命、更难以杀死的东西。
更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目前使用的大多数抗生素都被认为是“广谱”药物。从本质上说,它们被设计来杀死所有它们接触过的细菌,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中性的。它们不擅长处理特定的感染,更不用说发生基因突变的细菌了。由于同时消灭了有益细菌,这些广谱抗生素降低了我们免疫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当我们的防御能力下降时,耐抗生素的新菌株以及可能致命的超级细菌就会占据上风。简而言之,谈到现代抗生素时,现行标准的医疗程序是在我们真正需要狙击手的时候却使用了凝固汽油弹。
奇普瑟姆是越来越多科学家中的一员,他们相信存在一种智能的——但也复杂——解决方案。截至2016年,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生物学家估计,99.9999%的微生物物种(约1万亿种不同的微生物,它们的天然化学分泌物构成了所有抗生素的基础)仍有待发现。奇普瑟姆相信加拿大的铁幕洞穴——因为其丰富的铁矿床而得名——是我们找到这些新细菌并利用它们开发新抗生素的最佳机会之一。
对奇普瑟姆来说,寻找完美的洞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1970年,她出生于泰国的纳空萨旺(Nakhon Sawan),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她把自己对生物学的兴趣归功于父亲。“他在我11岁的时候从大学毕业,获得了生物学学士学位,”她解释说,“他常常带我去采集样本,我开始为此而着迷。”
▲图示:从左至右,来自洞穴钟乳石的未处理样本,采集的细菌,奇普瑟姆实验室墙上关于洞穴细菌的照片
1992年,奇普瑟姆在泰国北部的昌迈大学(Chang Mai University)完成了自己的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本科学位,开始与富田扶桑(Fusao Tomita)一起工作。富田扶桑曾是日本第三大制药公司Kyowa Hakko的研发部主管。在富田的指导下,奇普瑟姆将她在硕士和博士进修期间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从真菌中开发新的抗真菌药物。
在完成博士学业后,她于1999年回到泰国,继续在昌迈大学工作。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地球微生物学和生物学专家戴安娜·诺瑟普(Diana Northup)撰写了一篇有关洞穴细菌的文章,这说服了奇普瑟姆转向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研究。她解释说:“我想如果我进入一个更极端的环境,我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去发现新的东西。”
最初,奇普瑟姆搜寻极端环境中微生物的工作把她带到了泰国南部的红树林沼泽地带。但她有一种预感,自己在寻找洞穴时会更幸运。唯一的问题是,大多数可以进入的泰国洞穴都向游客开放,都是修筑了水泥路面、有人造灯光并摆着佛像,更不用说每周有数十人徒步出入。换句话说,这与那些稀有而独特细菌习惯于生长的原始环境正好相反。2001年,她和丈夫乔·多布森(Joe Dobson)一起搬到了他的家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次年在汤姆森·里弗斯(Thompson Rivers)开了家公司。
十年后,她发现了她可以称之为完美洞穴的东西。奇普瑟姆和她的同事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中概述了他们的初步发现,报告了在铁幕洞穴中发现的100种细菌。其中12.3%是未知的,甚至可能是全新的细菌。迄今为止,其中两种已被证明对抗多重耐药微生物菌株是有效的。
早春时节,我坐在一辆卡车的副驾驶座上,罗布·沃尔(Rob Wall)开车带我们穿过奇里瓦克盆地(Chilliwack Basin)偏僻的乡间小路前往洞穴。一望无际的树林从两旁延伸开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巨大地下洞穴网络。
在充满生命的森林深处,长满青苔的土丘一侧有一扇一米宽的金属门,就像某种蒸汽朋克时代霍比特人所居住的洞穴。只有沃尔和斯托罗辛斯基能够带人进去。一旦大门打开,你将下降10米(从一对两端相连的梯子)进入地球的内部。在那里你会发现半公里长得蜿蜒曲折石灰岩隧道,以及地下水池、幽闭的裂缝和天花板上悬挂的石笋,黑暗是这里的主人。
作为CRVC的一员,现年四十多岁的沃尔是铁幕洞穴的管理人,与政府合作控制通道。它的确切位置是保密的。而该地区的其他洞穴常常被周末游客破坏,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令沃尔大为懊恼。保护这种独特的资源是关键,而铁幕洞穴设置的金属门保护其不受上面世界的影响,进入者必须严格遵循灭菌程序,以防止探洞装置和科学仪器污染被隔离的细菌。
如果进洞者当天已进入另一个洞穴,则需要使用经过净化或全新的探洞设备。这是为了防止有机物质的交叉污染,而有机物质的交叉污染反过来又会破坏洞穴细菌特定的栖息地,可能会破坏独特的(可能有用的)细菌种群。通常情况下,进洞者都穿着一次性的Tyvek工作服,然后设备都密封在塑料袋里,并且在离开洞穴时喷洒消毒剂。最好穿橡胶底易清洗的靴子,在进入或离开任何洞穴前必须进行更换。当然,在采集样品时使用的科学设备要么必须经过消毒,要么必须以前没有使用过,并密封在包装中直到需要时才拿出来。
斯托罗辛斯基带领我们进入深邃的洞穴。他的工作是确保奇普瑟姆和她的团队——以及洞穴环境——在样本收集过程中的安全。虽然从技术上讲,铁幕洞穴并不像附近的其他洞穴那样具有挑战性,但洞穴内部也狭窄蜿蜒,需要有经验丰富的向导来带领前行。
斯托罗辛斯基和沃尔并不是唯一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新细菌的洞穴探险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洞穴探险联合会(BCSF)是该省洞穴探险者的联合组织,该组织旗下的一些洞穴探险者冒险进入区域内的各个地下洞穴,为奇普瑟姆收集样本。有一个洞穴处在灰熊的栖息地,所以需要洞穴探险者用直升机进入以避免遭到攻击。另一种洞穴需要探洞者潜水进入——这是大多数微生物学家无法企及的技术壮举。如果没有这些洞穴探险家没有报酬的辛勤付出,奇普瑟姆的研究就会停滞不前,而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也会继续不加控制地发展下去。
在我们呆在洞穴期间,斯托罗辛斯基带领我们在低矮的洞顶下穿过狭窄的通道,并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那些古老的洞穴墙壁。他还负责维护引导我们穿过洞穴的发光带条。偏离路径太远,不仅有损坏洞穴的风险,还会让自己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在洞的后面,锥形小径的边缘有一个一米宽的大洞通向看似无底的黑暗。“它会一直通向地心,”斯托罗辛斯基半开玩笑地说。
有一次,为了给我们的团队腾出空间,斯托罗辛斯基背靠着洞壁,一块拳头大小的松动石头砸在了他的背上。虽然没有受伤,规则要求他向我们发出危险警告,并下意识地离开了墙边。幸运的是,洞顶完好无损。
距离奇利瓦克东北约25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叫做坎卢普斯的大学城。穿过伐木场,越过需要给汽车加防滑链的垭口,以及被远山环抱的半干旱草原就到了这里。从2002年开始,奇普瑟姆就在汤普森里弗斯大学科学大楼三楼的一个L形小实验室里工作。
奇普瑟姆的实验室装饰着放大的洞穴细菌黑白照片,就像粉笔上的灰色小头。沿墙是一组不锈钢材质的生物安全柜,用于处理可能有害的洞穴样本。空气压力、氧气含量、光照和矿物质都促使细菌适应环境产生进化,但人们认为钙离子对细菌DNA链的侵入可能导致最大的变化,这会迫使细菌在遗传水平上做出适应,否则就会死亡。因此,奇普瑟姆将她的研究范围缩小到了由碳酸钙或硫酸钙沉淀形成的石吸管洞穴沉积物。
奇普瑟姆使用镊子或棉签采集洞穴样本,然后通过含有琼脂的安全壳运送到实验室,并保持在12°C的温度,模拟洞穴条件以维持微生物的存活。在本科生Richenda McFarlane和Keegan Koning的帮助下,奇普瑟姆尝试在隔离培养基上培养这些细菌之前,先从洞穴样本中分离出细菌——这是一个漫长而又遥远过程的第一步。
但是,要想让地下细菌在实验室里茁壮成长,必须精确复制它所形成的条件。用奇普瑟姆的话来说,这是“在黑暗中进行射击”。
“我们不知道每一种细菌想要在哪种培养基上生长,”奇普瑟姆承认。“我只能猜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生物、物理和化学因素,然后在实验室里试着去模仿。这永远不会是100%的,我们经常会错过很多东西。”
即使这种营养液被证明足以培养地下生命,也要等上很长时间。通常情况下,一些洞穴细菌需要2到8周的时间才能在实验室里生长。通过提供丰富的营养来促进洞穴细菌快速生长通常也不起作用。奇普瑟姆将这种方式比作“把沃尔玛超市堆在它们头上”。“毕竟在洞穴里,没有光线,他们获取的仅有一些有机物质要么是上方渗出的水,要么是其他方式。洞穴细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种环境。”
如果奇普瑟姆的团队能够分离出这种细菌,并且它的代谢产物显示出开始生长的迹象,那么就必须通过基因挖掘技术来对细菌基因组进行测序。然而由于资金紧张,奇普瑟姆所在的实验室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实验。其与远在4300公里外的渥太华大学化学和双分子科学系合作。在那里,生物化学主任克里斯托弗·博迪(Christopher Boddy)和他的博士生杰西卡·戈斯(Jessica Gosse)正在细菌中寻找一种与抗生素相关的遗传模式,这种遗传模式在过去曾被成功用于医疗。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个序列,他们就会评估细菌对多种病原体的抗生素活性,并试图更好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与Ann合作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上互补,”博迪解释说。“她是一名出色的微生物学家,在培养细菌方面有着一流的技能。我的实验室本质上更具分子特性。我们在这次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是测序Ann发现细菌的基因组,并利用基因组的信息来指导我们发现新的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
遗憾的是,对于博迪的团队来说,研发新型抗菌药物的任务已经具有个人意义。去年,戈斯失去了一位朋友,原因是患上了一种耐抗生素的细菌感染。
迄今为止,奇普瑟姆和她的汤普森里弗斯大学团队已经在铁幕洞穴中发现了100种新的细菌分离物,但目前只能对其中最有希望的两种进行研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奇普瑟姆叹了一口气。“我没有足够的学生或资金来进一步研究这种细菌。我们必须重点关注那些具有良好杀灭能力的细菌,并且是最稳定的。换句话说,每次我对其进行培养它们,都需要产生有用的代谢物。
然而,尽管奇普瑟姆尚不确定它们的用途,但在当前的危机中,即使是两种新的抗生素也似乎是一种有价值的援助。但是抗生素的开发过程远不是那么简单。“可能需要10到25年的时间才能在货架上买到一种新的抗生素,”奇普瑟姆说。“你认为会有大型制药公司会资助我们吗?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而且是一种冒险。我们可能在洞穴中发现100种细菌,但其中一些可能对某些细胞有毒。有些可能会同时杀死太多东西。想想制药公司以利润为导向的本质。研发一种新的抗生素需要10亿美元,而且每一剂抗生素的疗程只有7到10天。从效益上讲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尽管现实中存在奇普瑟姆的担忧,但对新药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自2014年以来,创新基金会Nesta已经为对抗生素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研究人员提供了高达800万英镑的奖励。既然奇普瑟姆存在资金问题,为什么基金会不给他们资助呢?
“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存在资金问题,”Nesta挑战奖中心奖项负责人丹尼尔·伯曼(Daniel Berman)解释说。500万英镑的奖金来自私人投资者。其他300万来自英国政府的英国创新计划。因此,奖金仅限于在英国活动的机构。即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资金,伯曼预测,另一个问题是,“资助者并不喜欢长期演技。如果你现在看看受资助药物的渠道,重点是帮助那些已经发现了可能新药的人,让他们为临床试验做好准备。
伯曼指出了AMR评论背后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的建议。奥尼尔提倡一种“市场准入奖励”制度,即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奖励基金。这些资金将被奖励给那些找到新抗生素的公司,从而让公司以较低的价格销售抗生素,而不是公司通过销售每一种抗生素来获得利润。但是,伯曼认为,这其中也存在固有的问题。广谱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只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免疫系统不断弱化,从而为新的超级细菌打开大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伯曼认为新的抗生素只能通过严格控制的处方来获得。
即使在一个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乐观世界里,为什么说开发新的抗生素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也另有原因。撇开极端微生物不谈,对研究过的细菌进行基因控制是开发新抗生素的唯一可能途径。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做法。但这远不可靠。“从1928年青霉素的引入,到1943年链霉素的引入,再到1980年代的达托霉素,通常在一两年内细菌就会产生耐药性,”奇普瑟姆说。“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制造出任何药物,细菌都将继续存在,并将继续流行。今天,我们的抗生素是对最初的核心抗生素的轻微改进。这就是为什么药剂师会谈论青霉素G, K, N, O, V等等。问题是人们只能在抗生素完全失效之前不断调整配方。”
尽管依旧面临着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奇普瑟姆和博迪仍然乐观地认为,他们会在某个地方发现一种新的细菌,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帮助人类。至少目前来看,我们只触及到了极端微生物的表面。
“任何环境都可能很有趣,”博迪说。“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从古代考古遗址到海洋等许多独特的地方。我们能够从海洋环境中培育出细菌只有15年的时间,而现在大量的新抗生素和抗癌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奇普瑟姆仍然不知道能否在她退休前找到新的抗生素。她说:“作为一名母亲,我至少会觉得我已经为我的儿子和未来几代人对抗多种耐药性感染尽了最大努力。”不管怎样,她仍然充满希望,解决全球日益严重抗生素危机的答案或许一直就在我们的脚下。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