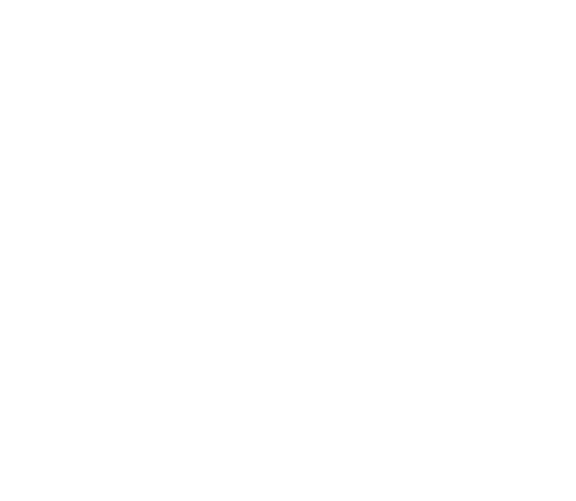多重宇宙理论的躁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缺乏实证的理论?
- 返朴
2022-11-03 19:0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George Ellis,翻译:刘一涵、张一
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物理学理论是否可以超越“可证伪”范式在物理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当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人们,包括物理学家在内,应该如何看待缺乏实证的理论?这样的科学理论还是科学的吗?本文可以看作有关争论的一种应答。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乔治・埃利斯(George Ellis)教授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多元宇宙的各种理论 —— 包括多达数十种不同类型的暴胀理论、人择原理等 —— 并考虑了一些与之相反的论点,由此得出结论:缺乏实验证明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 而且今后仍然如此。
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正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自 17 世纪以来,科学理论一直受到实验的束缚。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弦论(string theory)和多重宇宙理论(multiverse)摆脱了这一枷锁,它们的拥护者辩称,现在可不是理论屈服于实验的时代。
这正是奇怪之处。
同病相怜
多重宇宙是可能互不相连宇宙的总集、集合或系综。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否存在。泰格马克(Max Tegmark)设想过四种不同的多重宇宙,格林(B. Green)设想了九种 [1]。没有比这更多的了。
宇宙学家瑞斯(Martin Rees)认为,我们的宇宙不可能结束于可见视界(visual horizon)。他写道:“这层外壳并不比你身处海洋中央看到的边界更有物理意义。”[2] 在宇宙的可见视界之外,一定有我们所看不到的更远的领域。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有过类似的观点,毕竟他确实是对的。
古斯(Alan Guth)、林德(Andrei Linde)和维伦金(Alexander Vilenkin)都已经接受多重宇宙理论,因为它符合当前的一些宇宙学理论。在极早期宇宙的热大爆炸(Hot Big Bang)时期之前,几乎就是在大爆炸瞬间过后,出现了一段极速的指数膨胀时期。这一时期的各式膨胀很可能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宇宙,而这些多重宇宙的参数有很大不同 [3]。
多重宇宙同时出现于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萨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认为,弦论才是量子引力的正确理论。不同的弦真空截然不同,它们的物理性质因此不同,或可能变化。原则上说,每一个弦真空都代表一个宇宙。它们可能与膨胀的宇宙有关。因为没人能确定哪个才是真实宇宙,萨斯坎德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多重宇宙都是真实的。
彭罗斯(Roger Penrose)、斯莫林(Lee Smolin)、斯坦哈特(Paul Steinhardt)和图罗克(Neil Turok)都认为多重宇宙产生于时间而不是空间。就像斯莫林所提议的那样,每产生一个新的不断膨胀的宇宙,它们中的自然常数都是不同的,这就会导致无穷无尽的演化。但如果像彭罗斯所言,如果自然常数都相同,其结果就是永恒的归一。
卡洛尔(Sean Carroll)、多伊奇(David Deutsch)、泰格马克和华莱士(David Wallace)均声称,每次进行测量后,宇宙的量子波函数都会分裂出多个分支。每个分支即一个宇宙 [4]。这个想法最初由埃弗雷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在他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中提出。(编者注:参见《多世界的幻想:最奇特的科学理论其实不自洽》)多重世界因为波函数的分叉而出现,分叉之后,各个宇宙保持某种叠加态,完全遵从线性的、确定性的薛定谔方程,并且波函数从不塌缩(collapse)。埃弗雷特的方案并不需要玻恩规则(Born rule)。但后者确定了波函数振幅的平方是一种概率测度(measure of probability)。所以必须要有什么东西取代其位置或起同样作用。一些物理学家认为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many world)和多重宇宙的多重世界是同一的。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声称,多重宇宙对赋予量子力学概率预测以精准的操作意义是必要的 [5]。
刘易斯(David Lewis)和席阿马(Dennis Sciama)提出了一种模态实证主义的强形式 —— 可能即真实。(译者注:模态现实主义指,除了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能的世界。相信这种可能世界存在的人被称为模态实证主义者。参见,如,Philosophy of Logic,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7,997-1022. )一个可能的世界可以用一组最大程度上一致的判据来标识。一个刘易斯可能是南极洲皇帝的世界,和另一个他不是皇帝的世界,至少因这一判据而不同。否则这两个世界即是本体论上全同的。多重宇宙就是所有可能世界的集合。
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多重宇宙是否是一个恰当的科学对象?多重宇宙中判据为真的集合是什么?它不可能是某些宇宙中为真的判据的并集,因为这些并集前后矛盾。它也不可能是两者的交集,因为那样的话,就只剩下逻辑和数学的真理了。
泰格马克也不甘示弱,他认为所有一致性的数学结构都存在于一些互不连通的宇宙中。他还认为,宇宙中除了一致的数学结构之外皆是虚无。他自己本身就是个一致的数学结构。这一观点赋予了数学结构前所未有的能动性。
物理学常数经过了微调(finely tuned)[6]。生命不可能存在于微调温度范围以外的宇宙中。瑞斯(Martin Rees)确定了六个物理常数,其精准数值是生命的必备要素。它们分别是:N,电磁力与万有引力之比;ε,氢到氦的聚变效率的度量;Ω,宇宙的质量密度与其临界密度之比;Λ,假想的宇宙学常数;Q,将一个星系团分开所需的引力能与其等效质能之比;以及 D,空间维数。瑞斯认为,如果无量纲物理参数集合 C=<N, ε, Ω, Λ, Q, D> 稍有不同,生命就不可能形成。
温伯格、萨斯坎德、卡洛尔、泰格马克、霍金、莫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和瑞斯本人都辩称,在一个宇宙中不可能发生之事,在多重宇宙中则不可避免。
这些观点反响平平,也许是因为,如果 C 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那么生命存在本身就足以说明 C 具有它所有的价值。
视野之外
任何对宇宙的直接观察都受限于我们的可见视界。宇宙的热大爆炸阶段大约在 138 亿年前结束。在那之前,光线无法穿过宇宙。可见视界中的最远星系距我们约 3 × 138 = 414 亿光年。宇宙的膨胀速率并非恒定 —— 因此乘以因子 3。超出这个距离的宇宙根本无法被观测到。
我们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小到可以被包含在视界内的宇宙中。若果真如此,我们将在宇宙微波背景 (CMB) 中看到星系的多个图像和一些相同的圆。小宇宙可以排除掉多种多重宇宙(理论)。但如果宇宙没那么小,多重宇宙的问题就依旧没有定论。
粒子视界(particle horizon)指的是一个粒子从大爆炸或 t = 0 的时间起到当下的最大距离。在静态宇宙中,粒子视界可以定义为从 t = 0 开始流逝的时间与光速的乘积。但因为宇宙在膨胀,因此粒子视界必须被定义为光速和共形时间(conformal time)的乘积。共形时间是一种时间尺度,它通过对时间的缩放使得光速为 1。由于我们和粒子视界之外的东西 —— 如果有的话 —— 没有任何观测或因果联络,我们无法直接检验关于其性质的任何猜想 [7]。
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根据弦论的假设,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宇宙一定是开放的、具有负曲率 [8]。因此,任何关于我们的宇宙具有正曲率的观测,通过换质位法(Contraposition)(译者注:所谓换质位法,是形式逻辑的一种推理,指通过改变判断的质,从而推出一个新判断的直接推理。 ),都必然成为反对弦论的证据,也必然反对多重宇宙的导出 [9]。还有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多重] 宇宙之间的碰撞可能会在微波背景的天空中留下可观测的痕迹 [10]。如果能测量到这些痕迹,他们也许会支持多重宇宙的某些模型。
尚克斯(Tom Shanks)和他的研究生麦肯齐(Ruari MacKenzie)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上发表文章称,宇宙微波背景下的冷区(cold regions)可能是这种碰撞的证据 [11]。但这些冷区也可能是统计涨落的结果 [12]。
这并不是证实多重宇宙假说的有力证据。
暴胀
早期宇宙的暴胀理论断言,在大爆炸和热大爆炸时期之间,宇宙经历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但极高加速的膨胀期。这点似乎得到了数据支持 [13]。该理论由古斯提出,旨在解决经典大爆炸宇宙学中广为人知、但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 [14]。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在大尺度上温度是均匀的,宇宙背景辐射的均匀程度是 10 的五次方分之一。在经典的大爆炸宇宙学中,两个相距距离超过粒子视界的区域之间不可能达到热平衡。
暴胀宇宙学(Inflationary cosmology)提供了一种解释。这与进化生物学家在解释两个物种为何如此相似时给出的解释一样 —— 它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在同一空间区域上处于热平衡状态的粒子拥有共同的起源。暴胀引发了宇宙范围内的剧烈加速膨胀,同理,当因果历史追溯到大爆炸时,它也揭示了宇宙的急剧减速收缩。在标准的大爆炸宇宙学中永远不可能发生因果联系的两点,在暴胀理论下却可以找到处于同一空间区域的共同起源。
由此产生的平滑性正如我们在 CMB 中看到的那样。
暴胀的发生是因为膨胀因子的加速。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正标量场势 V (φ) 驱动暴胀。在经典的弗里德曼-罗伯逊-沃克(Friedmann–Robertson–Walker)宇宙情况下,标量场对于所有事物来说都相当于一种完美流体(perfect fluid)!暴胀理论包含一个庞大的模型体系,包括了旧暴胀、新暴胀、R2 暴胀、SUGRA (supergravity,超引力) 暴胀、双重(double)暴胀和幂律(power-law)暴胀、自然暴胀和混合暴胀(Natural and Hybrid inflation)、扩展(Extended)暴胀和辅助(Assisted)暴胀、超对称 F 项(SUSY,supersymmetry F-term)暴胀和 D 项(D-term)暴胀、膜(brane)暴胀,还有些叫超自然(supernatural)暴胀、SUSY P 项(SUSY P- term)暴胀、K 暴胀、扭曲膜(warped brane)暴胀、快子(tachyon)暴胀和轮盘(roulette)暴胀。
在宇宙学快速 Fortran 程序的 ASPIC 库中收录 70 多个可用的暴胀模型 [15]。通常假设暴胀场是某种被称为暴胀子(inflaton)的量子化粒子,但这一假设明显没有太大帮助。除非这个暴胀子被证明是希格斯玻色子,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进一步去发现它,毕竟对撞机实验所能达到的能量是有限的。要达到更高的能量,就需要对宇宙线进行观测,但我们还没发现任何可能和暴胀有联系的粒子。利用 CMB 数据可以对 V (φ) 的性质加以限制 [16]。萨斯坎德认为科尔曼 — 德卢西亚(Coleman–de Luccia)隧穿理论是暴胀的一种方式,但永恒暴胀理论(eternal inflation)的数学可行性尚无定论 [17]。
人择约束
爱因斯坦 —— 带着一些对膨胀宇宙的哲学上的厌恶 —— 把宇宙常数 Λ 引入了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因为没有它就无法获得场方程的静态解。当 Λ=0 时就回到爱因斯坦的原始场方程。当 Λ>0 时,场方程有一个静态解,对应一个充满尘埃的球形宇宙,其质量密度为 ρ=Λ/8πG。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常数对他的原始方程有变形作用。在这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他采用的静态解被证明不稳定 [18]。1920 年代,当哈勃(Edwin Hubble)提供了宇宙正在膨胀的惊人证据时 [19],爱因斯坦开始后悔引入了宇宙常数。他最初的方程与膨胀的宇宙相容。他高兴地对外尔(Hermann Weyl)说,“如果世界并不是准静态(quasi-static)的,那就把宇宙学(常数)项扔掉吧。”[20]
尽管如此,宇宙常数在广义相对论中一再出现。洛伦兹不变性表明场方程中可以出现一个有效宇宙学常数项 Λeff。这个宇宙常数为总的有效真空能贡献一个小量:
宇宙学观测表明,ρV 的绝对数值大约为 10-47 GeV4。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21]。在宇宙学中,宇宙学常数通常表示为由宇宙学常数产生的能量密度与宇宙临界密度之间的比值,ΩΛ。普朗克卫星数据表明 ΩΛ≈0.6911±0.0062。这个值很小,但也不是零。温伯格注意到:“我们对当前宇宙膨胀率的了解表明,宇宙学常数的有效值 Λ 远远小于任何已知的实际基本粒子理论中因量子涨落而产生的宇宙常数值。”[22]
量子场论显然不能很好地得出 Λ 的大小。
如果不用量子理论,还能用什么?温伯格补充道:“也许 Λ 必须足够小才能让宇宙进化到现在几乎空无一物的平滑状态,否则就没有科学家来忧心这个问题了。”[23] 温伯格将他的推论形式化,给出了 Λ 值的预言,但他的解释包含了很多情境限定词汇:也许(perhaps)、必须(must)、允许(allow)、否则(otherwise)。但是为什么 Λ 必须足够小或足够大才能包容万象?没有一个基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 Λ 应可以取不同的值。
像瑞斯和卡洛尔这样的物理学家支持温伯格的观点,因为它为人择约束的思想提供了内容:“宇宙学常数充要的人择论条件是,它不能太大使得引力束缚态无法出现。”[24] 这一考虑从上下限上同时严格限制了 Λeff 的大小。温伯格注意到:“如果 Λeff 是较大的正值,宇宙极早期进入指数膨胀的德西特阶段,然后一直持续下去。”[25] 这对生命的出现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如果 Λeff 为负值,宇宙会在某个时间坍缩成一个奇点,这段时间对生命进化而言可能太短。
为了确定上界,温伯格使用皮伯斯简单的球面下降模型 (spherical infall model) 来跟踪物质密度中不均匀性的非线性增长 [26]。他设想早期宇宙按照标准大爆炸宇宙理论进行演化,其中宇宙学常数为 Λ,宇宙背景空间曲率 k 为零。演化的宇宙受到均匀但非线性的扰动。它们是引力成团和星系形成的必经之路。宇宙的演化受均匀的过剩密度 Δρ(t)、正曲率常数 Δk>0,以及尺度因子 a (t) 的支配。扰动模型按照弗里德曼(Friedmann)方程:
其中根据定义 ρν=Λ/8πG。
扰动强度
温伯格接着考虑宇宙是否会发生再坍缩并导致凝聚,得出 Λ 的人择上限是,
这建立在宇宙导致大尺度结构的假设之上。
温伯格的论点纯粹是人择论的,它提供了对宇宙学常数的限制。正是多重宇宙理论的引入使温伯格能够根据适于多重宇宙产生生命的平均值来明确指出宇宙学常数的期望。只有当 ργ 可以变化时,其平均值和期望才有意义。既然它不能在任意给定的时间 t 内在一个宇宙中发生变化,那么在许多不同宇宙中它一定可以变化。谈论 ργ 的平均值,就是谈论它在宇宙的集合或系综(ensemble)中 M={U1, U2, …, Un, …} 中的平均值。
此中有真意
在任意宇宙 Uk 中 ργ 的绝对值,必须小于宇宙演化所需的质量密度。如果这一点是对的,ργ 只需小于星系形成时宇宙的质量密度。在与马特尔(Hugo Martel)和夏皮罗(Paul Shapiro)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温伯格继续推导出许多宇宙学常数的“可能值”[27]。这篇文章讨论的核心是假设定义于 M 之上的 Λ 形成一个概率分布,这一分布与“注定要从背景中凝结成物质比例”成正比 [28],这些物质的质量浓度足以形成观察者。这一比例是通过标准宇宙学理论,根据再复合时期的密度涨落计算出来的。将 ργ 的可能值与宇宙学常数的观测范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即便所有 ργ 值都具有相同的先验(a priori)概率,存在一个较小的正的 ργ 值也合情合理。
必须强调的是,温伯格的结论并没有证明多重宇宙的存在,多重宇宙只是论证的假设之一。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一致性测试。温伯格的计算考虑了 Λ 值的变化且只有 Λ 值变化。当其他常数同时变化时,结果是不同的 [29]。斯塔克曼(Glenn Starkman)和特罗塔(Roberto Trotta)注意到,如果赋予宇宙以概率的方式不同也将导致不同的人择预言:
在概率作为频率的框架内,人择推理并不明确(ill-defined),而且为何选择这一种权重方案而不选另一种,这一基础动机的缺乏使得人择原理无法用来解释 Λ 值,很可能,也无法解释其他物理参数的值 [30]。
这让人想起埃弗雷特的理论 [31]。无论如何,安鲁 (William Unruh) 等人对真空能的一项更复杂的分析表明,人们可以从量子场论中得出 Λ 的观测值而并不需要引入多重宇宙 [32]。
如梦幻泡影
多重宇宙几多重?只要宇宙可以无限膨胀,就像在永恒暴胀理论中那样,答案必然是宇宙最终会无穷多也 [33]。在数学的哲学中,潜在的无穷和实际的无穷之间有一个典型的区别:当借助后继函数 S (n) = n + 1 来定义自然数 1,2,3,…,时,它们永远保持为潜在的 [无穷]。它们对任何给定的 n 都是有限的,但对于所有自然数的集合则不然,后者的集合的势是ℵ0。继康托(Georg Cantor)之后,集合论学家认为它的确是实际意义上的无穷。它没有任何潜在的意义。物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实际意义上的无限持怀疑态度,且有充分的理由。希尔伯特旅馆(Hilbert Hotel)有无穷多的房间,让我们假定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然而,如果通过函数 f: n → n + 1 来移动其他每个房间的房客,总可以多出一个新的房间。这并非逻辑悖论,因为无穷不是一个具体数字。但物理学家们始终无法接受希尔伯特旅馆可以表达在任何一种物理实体上。
在几乎所有的暴胀情景下,宇宙的形成都是没有尽头的。如果多重宇宙是无穷多的,在任何时刻它们都可能是潜在无限的 [34]。但多重宇宙是它们全体的集合。如果自然无休止地创造它们,就像它连续不断创造自然数一样,那么多重宇宙的集合的势就是ℵ0。多重宇宙的所有子集的集合的势是 2ℵ0。
这是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如果多重宇宙并不合乎科学,那么哲学家们总是可以通过扩大科学的疆域来拯救它。这种论点认为,理论不需要经验证据来证实。达维德(Richard Dawid)在一篇名为《基础物理学中非经验证明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Non-Empirical Confirmation in Fundamental Physics)的论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在缺乏经验证实的情况下,科学家可以根据广泛的论据来判断一个理论的可行性。”[35]
达维德说,一顺百顺。满足条件的特定集合的理论在过去一直有效,这就增加了满足相同条件的新理论在未来继续奏效的可能性。这一论证体现了人们的希望对实验的重大胜利。1974 年,乔基(Howard Georgi)和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提出了一个精妙的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这个理论被冀望将强力和电弱力统一起来。它预言,由于自发对称性破缺(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质子将会衰变。这就是人们的希望。就目前实验所能确定的,质子并不衰变,此即经验。
达维德注意到,如果元归纳法(meta-induction)的确是一位严厉的老师,那么总会存在关于意外解释之间关联的争论。理论的发展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发现,理论一旦发展起来,就可以解释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问题。达维德认为这证明了理论的可行性。如果把既有物理理论与既有物理实体的世界联系起来,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这个想法并不能运用于某些纯数学的物理或宇宙学,或是理论的某些方面为获得所需的额外结果而进行了调整。令人惊奇的数学关系并不一定能在物理上实现。
达维德辩称,如果所有其他尝试都失败了,并且没有比某一理论更好的办法,那么它就聊胜于无。当然,在日常生活或者在物理学中,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时候得出“没有其他办法”这样的结论比较合适。缺乏想象力或者模型范围过窄都有可能。无论如何,这个观点并不可靠。如果一个理论为真,那么没有替代理论的事实实属多余,如果它非真,那更无关紧要了。对于多重宇宙的例子,有另外的选择:那就是不存在多重宇宙,我已经提到过了,安鲁等人提出的机制可以解释 Λ 值,或者只是碰巧被设定为使得引力符合幺模(unimodular)理论的值。
罗威利(Carlo Rovelli)回应达维德说:
科学家常常依靠非经验的论证来信任理论。在找到经验证据之前,他们会挑选、发展和相信理论。整个科学史都在佐证这一点。达维德用贝叶斯范式(Bayesian paradigm)来描述科学家如何评估各种理论。贝叶斯确证理论上使用的动词“确证”有其专业意义,这与外行和科学家的惯常用法有很大的不同。在贝叶斯理论中,“确证”指的是任何有利于论文的证据,无论多么薄弱…… 对于外行人和科学家这类人来说,“确证”另有含义:它意味着“非常有力的证据,足以让人接受理论是可靠的信念”…… 可靠理论和推测理论之间的区别可能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但却都是科学的基本要素…… 正是可靠理论的存在凸显科学对社会的价值…… 达维德的优点在于,他强调并分析了科学家在对理论进行“初步评价”时使用的一些非经验论证。他的缺陷在于混淆了这些非经验论证和 [经验] 证实之间的关键区别:证实是使一个理论变得可靠,被整个科学界接受,并对社会有应用潜力的过程。达维德的问题在于:他没能说明,在这一点上,只有经验证据才是有说服力的 [36]。
听听,听听!
参考文献
[1] 参见,Max Tegmark, Our Mathematical Universe: My Quest for the Ultimate Nature of Reality (New York: Knopf, 2014); Max Tegmark, “Parallel Universes,” Scientific American 288, no. 5 (2003): 40–51; Daniel Kleitman, “It’s You, Again,” Infer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cience 2, no. 3 (2016), and a letter in reponse, Sheldon Glashow, “A Hand-Waving Exact Science,” Infer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cience 2, no. 4 (2016); Brian Greene, The Hidden Reality: Parallel Universes and the Deep Laws of the Cosmos (New York: Knopf, 2011).
[2] Martin Rees, “Multiverse,” Edge (2017).
[3] Andrei Linde, “Eternally Existing Self-Reproducing Chaotic Inflationary Universe,” Physics Letters B 175, no. 4 (1986): 395–400; Alexander Vilenkin, Many Worlds in One: The Search for Other Univers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Alan Guth, “Eternal Inf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hysics A: Mathematical and Theoretical 40 (2007): 6,811–26. For an example of an inflationary universe that does not lead to a multiverse, see Viatcheslav Mukhanov, “Inflation Without Selfreproduction,” Fortschritte der Physik 63 (2015): 36–41, arXiv:1409.2335.
[4] David Deutsch, The Fabric of Reality: The Science of Parallel Universes—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York: Viking Adult, 1997).
[5] 参见,Raphael Bousso and Leonard Susskind, “The Multiverse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2011), arXiv:1105.3796; Dan Falk, “The Multiple Multiverses May Be One and the Same,” Nautilus (2017); Peter Woit, “Cosm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Not Even Wrong, May 19, 2011.
[6] 参见,Martin Rees, Just Six Numbers: The Deep Forces That Shape The Univer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Steven Weinberg, “Living in the Multiverse,”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Expectations of a Final Theory” at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September 2, 2005), arXiv:hep-th / 0511037; Leonard Susskind, The Cosmic Landscape: String Theory and the Illusion of Intelligent Design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5);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10).
[7] This will remain true if we consider observations for, say, another fifty thousand years.
[8] Ben Freivogel et al., “Observational Consequences of a Landscape,”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0603:039 (2006), arXiv:hep-th/0505232.
[9] 但是一些物理学家反驳了这一点,参见,Roman Buniy, Stephen Hsu, and Anthony Zee (2008) “Does String Theory Predict an Open Universe?” Physics Letters B 660, no. 4 (2008): 382–85, doi:10.1016 / j.physletb.2008.01.007.
[10] Anthony Aguirre and Matthew Johnson, “A Status Report on the Observability of Cosmic Bubble Collisions,” 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 74, no. 7 (2011), arXiv:0908.4105.
[11] 参见,“New Survey Hints at Ancient Origin for the Cold Spot,”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April 27, 2014; “Parallel Universes Do Exist and Researchers May Have the Strongest Evidence,” Physics-Astronomy, April 26, 2017.
[12] 对普朗克数据的标准解释在普朗克巡天团队报告中给出。参见,例如,Planck Collaboration et al., “Planck 2015 Results. XIII. Cosmological Parameters,”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594, no. A13 (2016), arXiv:1502.01589. 该报告并未提及多重宇宙。对冷点(cold spot)的解释有赖于使用的统计。参见,Ray Zhang and Dragan Huterer, “Disks in the Sky: A Reassessment of the WMAP ‘Cold Spot’,” (2009), arXiv:0908.3988v2.
[13] Planck Collaboration et al., “Planck 2015 Results. XIII. Cosmological Parameters,”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594, no. A13 (2016), arXiv:1502.01589.
[14] Alan Guth, The Inflationary Universe: The Quest for a New Theory of Cosmic Origins (New York: Perseus Books, 1997).
[15] ASPIC (Accurate slow-roll predictions for inflationary cosmology,暴胀宇宙学的精准慢滚预言).
[16] Jerome Martin, Christophe Ringeval, and Vincent Vennin, “Encyclopaedia Inflationaris,” Physics of the Dark Universe 5–6 (2014): 75–235, arXiv:1303.3787v3.
[17] Ikjyot Singh Kohli, and Michael Haslam, “Mathematical Issues in Eternal Inflation,” Classical and Quantum Gravity 32, no. 7 (2015), arXiv:1408.2249.
[18] 这一点由 Arthur Eddington 所论证。参见他的“On the Instability of Einstein’s Spherical World,”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90 (1930): 668–78.
[19] 哈勃基于 Vesto Slipher 的早期工作而建。
[20] Albert Einstein, 1923c. 致外尔的明信片 (Postcard to Hermann Weyl, May 23, 1923). ETH-Bibliothek, Zürich, Einstein Archive.
[21] 参见,Steven Weinberg,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Problem,”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61, no. 1 (1989): 1–23; Sean Carroll,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Living Reviews in Relativity 4, no. 1 (2001), arXiv:astro-ph / 0004075v2.
[22] Steven Weinberg, “Anthropic Bound on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59 (1987): 2,607, doi:10.1103/PhysRevLett.59.2607.
[23] Steven Weinberg, “Anthropic Bound on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59 (1987): 2,607, doi:10.1103/PhysRevLett.59.2607.
[24] Steven Weinberg, “Anthropic Bound on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59 (1987): 2,608, doi:10.1103/PhysRevLett.59.2607.
[25] Steven Weinberg,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Problem,”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61, no. 1 (1989), doi:10.1103/RevModPhys.61.1.
[26] P. J. E. Peebles: “The Gravitational Instability of the Universe,”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147 (1967): 859.
[27] Hugo Martel, Paul Shapiro, and Steven Weinberg, “Likely Values of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492 (1998): 29
[28] Hugo Martel, Paul Shapiro, and Steven Weinberg, “Likely Values of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492 (1998): 29.
[29] Anthony Aguirre, “On Making Predictions in a Multiverse: Conundrums, Dangers, and Coincidences,” in Universe or Multiverse? ed. Bernard Car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67–86, arXiv:astro-ph/0506519.
[30] Glenn Starkman and Roberto Trotta, “Why Anthropic Reasoning Cannot Predict Λ,”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97, no. 20 (2006), arXiv:astro-ph/0607227v2.
[31] Andrei Linde and Mahdiyar Noorbala, “Measure Problem for Eternal and Non-Eternal Inflation,” Journal of Cosmology and Astroparticle Physics 1009:008 (2010), arXiv:1006.2170.
[32] Qingdi Wang, Zhen Zhu, and William Unruh, “How the Huge Energy of Quantum Vacuum Gravitates to Drive the Slow Accelerating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Physical Review D 95, no. 103,504 (2017), arXiv:1703.00543.
[33] 参见,Alexander Vilenkin, Many Worlds in One: The Search for Other Univers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34] 注意此处的陈述“在任意时刻”(at any moment) 为何意存在显著的困难。George Ellis and William Stoeger, “A Note on Infinities in Eternal Inflation” General 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 41, no. 7 (2010): 1,475–84, arXiv:1001.4590.
[35] Richard Dawid, “The Significance of Non-Empirical Confirmation in Fundamental Physics,” (2017), arXiv:1702.01133.
[36] Carlo Rovelli, “The Dangers of Non-Empirical Confirmation,” (2016), arXiv:1609.01966.
作者简介
George Ellis (乔治・埃里斯) 是南非好望角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复杂系统荣休杰出教授。埃里斯教授的研究领域横跨引力和宇宙学、复杂性和因果关系、大脑和行为三大领域,从观察宇宙不同尺度的不同性质到研究人类大脑中基本情感系统的本质。埃利斯教授著作等身,迄今已经发表了 500 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早在 1973 年,他就和斯蒂芬霍金一起合作出版了名著《时空大尺度结构》(The Large Scale Structure of Space-Time)。他最近的著作是《物理学如何奠定思维?人类背景下自上而下因果的关系》(How Can Physics Underlie the Mind? Top-Down Causation in the Human Context),施普林格出版社 2016 年出版。
本文经作者授权译自:Physics on Edge, https://inference-review.com/article/physics-on-edge, DOI: 10.37282/991819.17.34。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