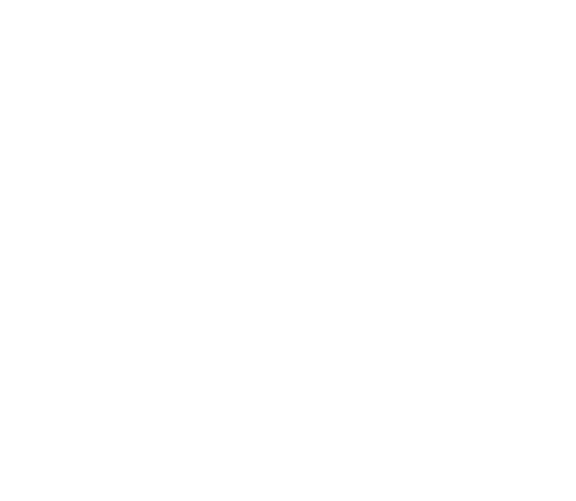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数学诺贝尔奖”的迷思
- 返朴
2022-11-15 21:3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倪忆(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
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奖“诺贝尔奖”并未设立数学奖,或许是这个奖项的最大缺憾。但因为诺奖的影响力巨大,其他未被纳入的领域也都有着自己的“诺贝尔奖”。数学家们就有自己的菲尔兹奖。事实上,菲尔兹奖与诺贝尔奖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它对获奖者年龄的严格限制。它最初并未定位为数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却因为政治事件的偶然影响获得了“数学诺贝尔奖”的美誉;如今还因为年龄、性别等因素存在争议。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这项大奖?回首菲尔兹奖的设立与颁发,我们能看到这一影响人类智慧历程的奖项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诺贝尔奖的缺憾
1896 年 12 月 10 日,瑞典化学家和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逝世。根据他的遗嘱,他留下的庞大财富被用来创立了诺贝尔奖。从 1901 年开始,诺贝尔奖每年颁发给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领域,只有极少数年份空缺。
那么问题来了: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诺贝尔奖中为什么没有数学奖?
坊间颇为流行的一个传言是,诺贝尔曾经因为个人感情问题跟瑞典数学大师米塔-列夫勒(Gösta Mittag-Leffler,1846-1927)结仇,故此不设数学奖。这当然完全是无稽之谈。没有证据表明诺贝尔和米塔-列夫勒之间有任何恩怨。事实上,作为瑞典科学界的领袖人物,米塔-列夫勒积极参与了诺贝尔奖的相关工作。在他的极力推荐下,诺贝尔奖才有了第一位获奖的理论物理学家 —— 洛伦兹(Hendrik Lorentz,1853-1928),以及第一位获奖的女性 —— 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米塔-列夫勒还多次在自己家中为诺贝尔奖得主举办庆祝宴会。[1]
巧合的是,日后提议设立数学奖章的菲尔兹(John Charles Fields,1863-1932)跟米塔-列夫勒有着深厚的友谊。[2] 所以菲尔兹奖的设立有时被人解读为菲尔兹给米塔-列夫勒出气。
诺贝尔数学奖的缺失让一些数学家感到失望。米塔-列夫勒早在 1884 年就试图劝说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1829-1907)设立一个数学奖,每四年颁发一次。但最终设立的是一个一次性的悬赏奖项 —— 关于多体问题的征解,获奖者是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854-1912),其获奖论文开创了动力系统这门数学分支。米塔-列夫勒在 1916 年又提议比照诺贝尔奖设立一个数学金质奖章,但没有奖金,奖品是他所创立的数学杂志 Acta Mathematica。这一提议也未能实现。[1]
当时瑞典和挪威组成了一个共主邦联“瑞典-挪威联盟”。挪威数学家索菲斯・李(Sophus Lie,1842-1899)在他去世前夕提议设立一个“阿贝尔奖”,从 1902 年开始颁发,以纪念天才的挪威数学家阿贝尔(Niels Abel,1802-1829)诞辰一百周年。由于种种原因,李的提议最终未能实现。[4] 直到一百年后,挪威政府才在阿贝尔诞辰二百周年之际设立了阿贝尔奖,并在 2003 年首次颁发。
ICM、UMI 与菲尔兹奖的设立
为了纪念阿贝尔诞辰二百周年,挪威还申办了 2002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但败给了中国。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ICM)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 1897 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 ICM 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届,因为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在这届大会上提出了 23 个重要的未解决问题。从巴黎大会开始,ICM 每四年举办一次,其间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
1908 年在罗马举办的 ICM 上,颁发了一个以意大利数学家古奇亚(Giovanni Guccia,1855-1914)名字命名的古奇亚奖章(Medaglia Guccia),获奖者是塞弗里(Francesco Severi,1879-1961)。但这一奖项并未延续下去。[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撕裂了国际数学界。1920 年在斯特拉斯堡举办的 ICM 上,成立了国际数学联盟(法语 Union Mathématique Internationale,UMI),负责组织 ICM。然而这个联盟并没有那么国际化:在法国数学界头面人物的坚持下,德国等同盟国成员国被排除在 UMI 之外,同盟国的数学家们也不被允许参加 ICM。[5] 事实上,这次 ICM 的举办地点本身就是对德国的羞辱:斯特拉斯堡在 1871 年,普法战争之后,被割让给德国;在 1918 年,一战之后,才刚刚回归法国。
直到 1928 年,同盟国数学家才被允许参加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 ICM,希尔伯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得到了全场的起立鼓掌。然而,各国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就此消除,国际数学联盟的活动中仍然充斥着政治争论。1932 年,国际数学联盟被迫解散。[5]
1924 年的 ICM 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这是 ICM 第一次在欧洲之外举行。大会组委会主席是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秘书则是辛祺 [注](John Lighton Synge,1897-1995)。菲尔兹在美洲接受教育,后来又到法德两国度过十年,跟欧洲数学界关系良好。菲尔兹为多伦多大会的筹办花费了很多心血。那个年代数学的中心在欧洲,让大批欧洲数学家跨越大洋来到美洲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当时科学界缺乏稳定的研究经费,菲尔兹设法从加拿大自治领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筹集到许多钱,解决了大会的财务问题。他又到欧洲访问了几个月,协调大会的各种组织工作。[2]
注:Synge 读音同 sing,常见译名有“辛吉”、“辛格”、“辛”等等,本文采用钱伟长先生在《八十自述》一文中的翻译。
多伦多大会后,菲尔兹花费四年时间,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完成这项工作后,会议经费仍然结余 2700 加元。于是在 1931 年,菲尔兹领导的组委会决定将其中的 2500 加元拿出来,在下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两个金质奖章。[5]
为了成功设立奖章,菲尔兹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同美、法、德、意、瑞士等国的数学会商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他还联系了加拿大雕塑师麦肯锡(R. Tait McKenzie,1867-1938),请后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奖章。菲尔兹本来准备在 1932 年 9 月举行的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正式提出设立奖章的议案,然而他不幸在大会前一个月病逝。临终前,在辛祺的见证下,菲尔兹将自己一部分遗产约 47,000 加元捐赠给奖章基金。在 1932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辛祺代替菲尔兹提出的永久性设立奖章的议案被接受。[5]
菲尔兹并不赞同 UMI 和 ICM 对同盟国数学家的排斥。在他写下的提案中,他反复强调这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奖章,对获奖者没有国籍限制。他写道,奖章上应该使用拉丁语或者希腊语,其设计不能跟任何国家、机构或个人联系起来。菲尔兹把这一奖章称为“国际数学杰出发现奖章”(International Medals for Outstanding Discoveries in Mathematics)。然而,这一奖项最终被命名为“菲尔兹奖章”,违背了菲尔兹本人的意愿。[6]
菲尔兹奖章由 14K 的黄金制成。奖章正面的头像是阿基米德,文字为拉丁文“Transire suum pectus mundoque potiri”,意即“超越人类极限,掌握宇宙”。背面图案是阿基米德墓碑上的几何图形:球的外切圆柱体。文字同样是拉丁文“Congregati ex toto orbe mathematici ob scripta insignia tribuere”,译为“全世界数学家聚集起来,荣耀对知识的重要贡献”。
在设立之初,菲尔兹奖的奖金是 1500 加元。从 1983 年华沙 ICM 开始,奖金额度多次增加,目前是 15000 加元。这跟百万美元级别的诺贝尔奖比起来微不足道,更远不能跟近年来热度很高的科学突破奖相比。但菲尔兹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远高于其他数学奖。即便是数学界影响不逊于菲尔兹奖的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其知名度也远远不能跟菲尔兹奖相比。
笔者当年在新东方上课时曾经听过俞敏洪校长的励志演讲,其中谈到俞敏洪的一位数学家朋友,在美国大学任教。这位朋友的志向是获得菲尔兹奖,俞敏洪便问他:“奖金是多少钱?”听到朋友的回答后,俞说:“这么一点钱,我给你好了!”朋友说菲尔兹奖的价值不止于此,菲尔兹奖得主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能拿到多少万美元的年薪,如果自己 40 岁还拿不到菲尔兹奖就改行。俞这才满意,称赞这位朋友有一个明晰的人生目标。
早期菲尔兹奖的颁发
在菲尔兹的提案里,这个奖章既是对已有成就的认可,也是对获奖者未来工作的鼓励。这一规则被解读为,奖章只颁发给“年轻”数学家,尽管早期颁奖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
1936 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获奖者是 29 岁的阿尔福斯(Lars Ahlfors,1907-1996)和 39 岁的道格拉斯(Jesse Douglas,1897-1965)。卡拉西奥多里(Constantin Carathéodory,1873-1950)在大会上介绍了两位获奖者的工作。那时菲尔兹奖远没有今天这么风光,没有一位获奖者此前听说过它。有人事先祝贺阿尔福斯获奖,但他在进入会场之前都没有得到正式通知。另一位获奖者道格拉斯虽然到了奥斯陆,但因为旅途过于疲劳,没有出席颁奖仪式,而是由他的同事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代替领奖。[5]
下一届 ICM 预定于 1940 年在美国麻省剑桥市举行,却因为二战而推迟了十年,直到 1950 年才得以召开。这时的数学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成为新的世界数学中心,新的国际数学联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 IMU)被组建起来。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1915-2002)和塞尔伯格(Atle Selberg,1917-2007)在这届大会上获得了菲尔兹奖,哈拉德・玻尔(Harald Bohr,1887-1951)介绍了他们的工作。
在玻尔的讲话中,提到评奖委员会一致认为菲尔兹奖应该颁发给非常年轻的数学家,但并没有明确“年轻”的意思。事实上,这届菲尔兹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本来是施瓦茨的法国同胞,44 岁的韦伊(André Weil,1906-1998)。作为评奖委员会主席的玻尔坚决反对给韦伊颁奖。在他看来,韦伊年龄过大,而且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他指出,颁奖给韦伊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会给人们一种印象,即委员会试图选定最伟大的数学天才。” 为了排除韦伊,玻尔建议把获奖年龄定为不超过 42 岁。玻尔的观点在评委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辩,按玻尔的说法,“需要血和泪”才能决定最后的获奖人。[7]
玻尔代表着早期菲尔兹奖颁发的一种倾向,即菲尔兹奖不是为了奖励最好的数学家,而是鼓励那些有潜力的数学家。如果菲尔兹奖不自我定位为“颁发给最好的数学家”,就能避免随之而来的各种比较和争论。菲尔兹本人的提案中就写道,在评论获奖者时应该避免“令人反感的比较(invidious comparisons)”。国际局势导致的割裂给那一代数学家们留下了过于沉痛的回忆,所以他们不想让菲尔兹奖的评审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1958 年,31 岁的希策布鲁赫(Friedrich Hirzebruch,1927-2012)是菲尔兹奖的大热门,但他却早早出局,原因是评委会主席霍普夫(Heinz Hopf,1894-1971)认为希策布鲁赫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认可,不需要进一步的鼓励。同样的情况在 1958 年和 1962 年两次发生在格罗滕迪克(Alexander Grothendieck,1928-2014)身上。[7] 在那个时候,菲尔兹奖根本没有“数学最高奖”的地位,所以菲尔兹奖得主也不被自动当作最好的数学家。
1966,数学与政治
1966 年是菲尔兹奖发展史上的关键一年,这一届的 ICM 在莫斯科举行,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菲尔兹奖也正是在这一年定型。
在 1966 年的两年前,印度塔塔信托基金会决定在 ICM 上设立一个塔塔奖,像菲尔兹奖一样,每届颁发两人。这一奖项未能设立,因为当时的印度国内政策不允许塔塔基金会向国外汇款。幸好有一位匿名人士捐了一笔钱,使得菲尔兹奖在这届可以颁发给四个人。从此形成制度,菲尔兹奖每届最多颁发四人。[5]
菲尔兹奖的另一个改变,是德拉姆(Georges de Rham,1903-1990)所主导的评奖委员会正式把获奖者的年龄限制确定为 40 岁。具体而言,获奖者的 40 岁生日不能在大会当年的 1 月 1 日之前。[5] 或许是因为明确了年龄限制,评奖委员会不再对给成名数学家颁奖有所顾忌。这一年的四位获奖者是:阿蒂亚(Michael Atiyah,1929-2019),科恩(Paul Cohen,1934-2007),格罗滕迪克和斯梅尔(Stephen Smale,1930-)。其中阿蒂亚和格罗滕迪克都可跻身二十世纪最伟大数学家之列,科恩和斯梅尔则是因为解决了数学界人尽皆知的难题而获奖。可以说这一届评选树立了一个标杆,从此菲尔兹奖便是以选出“未满 40 岁的最好的数学家”为目标。
前述的是制度上的变化。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让菲尔兹奖真正出圈,获得了“数学诺贝尔奖”的美誉。
在 1966 年的四位菲尔兹奖得主中,格罗滕迪克和斯梅尔都有着强烈的政治观点。格罗滕迪克为了表示对苏联当局的抗议,没有前往莫斯科参加大会。斯梅尔则坚定地反对越战,积极参与了许多反战活动,因此被美国政客盯上。1966 年夏,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向斯梅尔发出传票,要求他到国会接受质询。这个国会听证会的日期正好是斯梅尔领取菲尔兹奖的同一天。斯梅尔整个夏天都在欧洲访问,没有接到传票。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斯梅尔遇到了匈牙利数学家埃尔德什(Paul Erdős,1913-1996),从后者那里才得知传票的事情。[8]
抵达会场后,斯梅尔收到朗(Serge Lang,1927-2005)的一封信。信中告知斯梅尔《旧金山观察者报》的一份报道,里面称伯克利数学系教授斯梅尔躲开了美国国会传唤,前往莫斯科,字里行间暗示斯梅尔已经叛逃了。[8] 斯梅尔的同事们对此报道感到哭笑不得,连忙对媒体解释,斯梅尔只是去莫斯科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时领取菲尔兹奖。为了便于记者们理解,他们就说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的诺贝尔奖。这一说法被各大媒体引用,从此深入人心。(有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媒体还是采用了“美国数学教师获得苏联奖励”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7]
菲尔兹奖的争议
“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诺贝尔奖”这个简单粗暴的说法容易为大众所理解,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数学界在公众面前的话语权。斯梅尔后来因为从事反战活动,差点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取消科研经费,但“数学诺贝尔奖”的光环保护了他。[7] 许多地方都会给菲尔兹奖得主以诺贝尔奖得主的同等待遇。例如在斯梅尔工作的伯克利,菲尔兹奖得主和诺贝尔奖得主一样,可以享用校内的专用停车位。
虽说有着“数学诺贝尔奖”之称,但菲尔兹奖跟诺贝尔奖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诺贝尔奖经常会表彰某项工作的两到三名合作者,例如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沃森(James Watson,1928-)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就是同时获奖,但菲尔兹奖从未如此颁奖,尽管有越来越多的重要工作是多名数学家合作完成。
菲尔兹奖跟诺贝尔奖更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年龄限制。有人开玩笑说,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好事,这样数学家过了 40 岁后就不必再考虑获菲尔兹奖,不需要每年等待来自瑞典的深夜电话。虽说是玩笑,但 40 岁的年龄限制,确实让菲尔兹奖和诺贝尔奖对学科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菲尔兹奖颁发给年轻数学家,获奖工作通常为当前研究热点,而且这些人将来还会活跃二三十年,发挥影响的时间则可能更长。诺贝尔奖没有年龄限制,获奖者往往过了创造高峰期,很多人甚至已经退休。年龄最大的诺奖得主,“足够好”老爷子(John B. Goodenough,1922- ),在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已经 97 岁。所以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是对既往重大成果的追认,并不经常直接引导学科发展的潮流,这一点在近年来尤为明显。
以菲尔兹奖作为“数学最高奖”的定位而言,年龄限制隐含着不公平。乍一看,菲尔兹奖的年龄限制对所有人一样,都是 40 岁以下。可是,ICM 每四年才举行一次,不同年份出生的数学家能够获得菲尔兹奖的最大年龄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下次国际数学家大会将于 2022 年在圣彼得堡召开,届时 1981 年出生的数学家就失去参选资格。1981 年出生的数学家最后获奖的机会是 2018 年,那时他们 37 岁,需要跟 1978 年出生的 40 岁的数学家竞争。要知道,重大数学成果做出来花费的时间通常要以年计,得到广泛认可又需要几年,三四年的时间差距不是可以忽略的。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施拉姆(Oded Schramm,1961-2008),他在几何、拓扑、概率等领域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施拉姆最著名的工作是他所引进的 SLE,即随机勒夫纳演化(Stochastic Loewner Evolution),又称施拉姆-勒夫纳演化(Schramm-Loewner Evolution)。这一理论把随机过程与共形几何结合起来,解决了概率论和统计力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施拉姆有两位主要合作者,劳勒(Gregory Lawler,1955- )和维尔纳(Wendelin Werner,1968- )。其中维尔纳在 2006 年获得菲尔兹奖,劳勒在 2019 年获得沃尔夫奖,获奖的主要原因都是他们在 SLE 上的工作。2010 年菲尔兹奖得主斯米尔诺夫(Stanislav Smirnov,1970- )的部分获奖工作也是在 SLE 这一领域。
然而,作为 SLE 理论的创始人,施拉姆由于年龄原因未能获得菲尔兹奖,又因为过早离世而未能获得沃尔夫奖。施拉姆出生于 1961 年 12 月 10 日。在他因登山事故遇难后,《纽约时报》的讣告里写道,如果施拉姆晚出生三周又一天,那么他几乎必然会获得 2002 年菲尔兹奖。可是,如果一位优秀数学家仅仅由于这样微小的年龄差异就错过菲尔兹奖,那么菲尔兹奖又何谈是数学最高奖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菲尔兹奖的年龄限制对女性不公平,因为女性年轻时往往会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会耽误一到数年的科研时间。具体可参见《“青年数学家”神话与数学界的结构性性别不平等》一文。迄今为止,仅有一名女数学家米尔扎哈尼(Maryam Mirzakhani,1977-2017)获得菲尔兹奖。
即便对于符合年龄条件的数学家来说,菲尔兹奖的评选也难言绝对公平。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体育比赛的成绩可以用数字来表示,数学成果又如何能够量化?不同领域之间又如何能够比较?菲尔兹奖得主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跟评委会成员的偏好息息相关。正如菲尔兹、玻尔等先辈所预料,评选伴随着大量的争议,其中甚至不乏政治因素的参与。在 2014 年菲尔兹奖公布后,1998 年菲尔兹奖得主高尔斯(Timothy Gowers,1963- )在博客中指出,这一届有许多数学家,包括不止一名女数学家,也同样值得获奖。当然,这种情况绝非 2014 年这一届所独有,也绝非菲尔兹奖所独有。任何科技奖的评选都会有类似争议,但菲尔兹奖的年龄限制导致大多数被提名者只有一两次机会能够得奖,所以争议更显突出。
除了菲尔兹奖,数学界还有一些没有年龄限制的奖项,作为对数学家最高成就的奖励。这其中包括沃尔夫奖、阿贝尔奖、陈省身奖、科学突破奖等等。其中,阿贝尔奖在名称、颁奖国、评奖规则、奖金额度等诸多方面都与诺贝尔奖非常相似,近年来常被媒体拿来跟诺贝尔奖比较,可能更符合“数学诺贝尔奖”的定位。
回顾菲尔兹奖的历史,它最初并没有被设计成“数学最高奖”,却在阴差阳错之下得到了“数学诺贝尔奖”的美誉。但菲尔兹奖在制度上的先天缺陷又让它难以真正承担起“数学最高奖”的职责。所以有人提出,让菲尔兹奖回归初心,褪去“数学最高奖”的光环,仅当作是对优秀青年数学家的激励。[7] 这,或许才是对待菲尔兹奖的正确心态。
附录:IMU 颁发的其余奖项
除了菲尔兹奖以外,IMU 还设立了一些奖项,同样在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这些奖项每届均只颁发一人。以下对这些奖项作简要介绍。
IMU 算盘奖(IMU Abacus Medal),原名奈凡林纳奖(Rolf Nevanlinna Prize)
奈凡林纳(Rolf Nevanlinna,1895—1980)是芬兰著名数学家,曾担任 IMU 主席,1962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 ICM 主席,以及 1978 年芬兰赫尔辛基 ICM 名誉主席。为纪念奈凡林纳,赫尔辛基大学出资设立了奈凡林纳奖,奖励在信息科学的数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奈凡林纳奖也有 40 岁的年龄限制,从 1982 年开始颁发,目前奖金为 1 万欧元。奈凡林纳曾与纳粹势力合作,是其人生一大污点,故此 IMU 决定从 2022 年开始将奈凡林纳奖更名为 IMU 算盘奖。
高斯奖(Carl Friedrich Gauss Prize)
德国数学会和 IMU 利用 1998 年柏林 ICM 结余经费设立了高斯奖,奖励对数学以外的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数学研究。高斯奖没有年龄限制,从 2006 年开始颁发,目前奖金为 1 万欧元。
陈省身奖(Chern Medal)
陈省身先生(1911—2004)逝世后,他的家属和友人出资设立了陈省身奖,作为数学家的终身成就奖。陈省身奖没有年龄限制,从 2010 年开始颁发。陈省身奖的奖金额度为 50 万美元,其中 25 万美元给获奖者,25 万美元捐献给获奖者指定的机构,以支持数学研究、教育和普及。
里拉瓦蒂奖(Leelavati Prize)
2010 年印度海得拉巴 ICM 闭幕式上,颁发了里拉瓦蒂奖,用以奖励数学的公众普及。印度著名 IT 公司 Infosys 随后出资,将里拉瓦蒂奖作为 IMU 的常设奖项。《里拉瓦蒂》(Līlāvatī)是古代印度数学家婆什迦罗第二(Bhāskara II,约 1114— 约 1185)撰写的一部数学著作。里拉瓦蒂奖是 IMU 奖项中唯一一个在 ICM 闭幕式而不是开幕式上颁发的奖,也是唯一一个不奖励数学研究的奖。里拉瓦蒂奖的奖金额度是 100 万印度卢比。
拉德任斯卡娅奖(Ladyzhenskaya Medal)
拉德任斯卡娅(Olga Ladyzhenskaya,1922—2004)是俄罗斯著名数学家,曾被提名 1958 年菲尔兹奖。俄罗斯国家数学委员会、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 2022 圣彼得堡 ICM 组委会联合设立了拉德任斯卡娅奖,用以奖励数学物理及相关领域的革命性成果。拉德任斯卡娅奖没有年龄限制,奖金是 100 万卢布,将在 2022 年 ICM 期间一个纪念拉德任斯卡娅百年诞辰的仪式上首次颁发。
致谢:许晨阳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本文部分地受到了他的演讲《菲尔兹奖的魔咒》的启发。
参考文献
[1] Arild Stubhaug, Gösta Mittag-Leffler. A Man of Conviction. Springer-Verlag, Berlin, 2010. x+733 pp.
[2] J. L. Synge, John Charles Fields. J. London Math. Soc. 8 (1933), no. 2, 153-160.
[3] Michael Barany, The myth and the medal. Notices Amer. Math. Soc. 62 (2015), no. 1, 15-20.
[4] 阿贝尔奖官网,The History of the Abel Prize.
[5] Olli Lehto, Mathematics without borders.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998.
[6] Henry Tropp,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Fields Medal. Historia Math. 3 (1976), no. 2, 167-181.
[7] Michael Barany, The Fields Medal should return to its roots. Nature 553, 271-273 (2018).
[8] Steve Smale, On the Steps of Moscow University. From Topology to Compu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malefest (Berkeley, CA, 1990), 41-52, Springer, New York, 1993.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