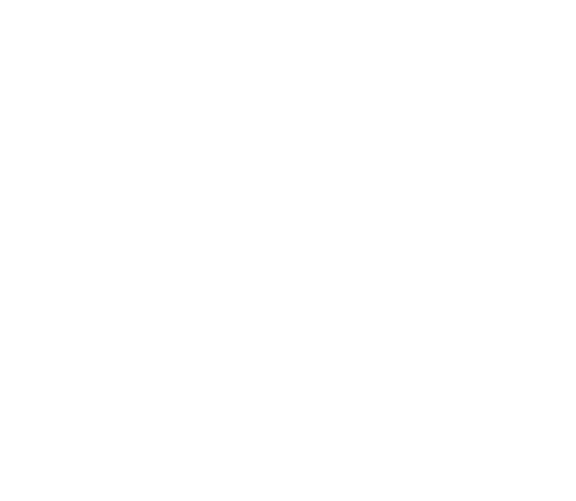达尔文的植物学:超前了 100 年
- 科学元典
2022-12-06 17:05
一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是全能型的博物学家,他在博物学的各个领域都卓有建树。
然而,人们对他在植物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一般而言知之甚少,尽管他在《物种起源》中引述了许多植物学方面的证据,而且在余生岁月中主要从事植物学研究,并出版了六部植物学著作。其中三部是关于花的植物学或繁殖生物学的,影响尤为深远: 《兰科植物的受精》(1862)、《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1876)以及《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1877)。一如围绕着达尔文的许多佯谬与悖论一样,深究这些怪象,对理解达尔文对演化植物学与植物生态学的重大贡献,既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
不少人可能一直存在一种错觉:青年达尔文乘小猎犬号战舰环球科考,途经加拉帕戈斯群岛,在相距很近的不同小岛上,见到了喙部形状各异的地雀;他受到了这一观察的启发,遂产生了物种可变的想法,回到英国后,便写出了震惊世界的不朽经典《物种起源》。
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达尔文对物种固定论产生怀疑,始于他在南美发现类似于现生大树懒的贫齿类哺乳动物化石。而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他对各个小岛上植物本土化的印象,远比对地雀本土化的印象更为深刻。正如科恩等人 2005 年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指出的那样,达尔文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受其良师益友、植物学教授亨斯洛 (J.S.Henslow,1796—1861) 先生的影响最大,在植物学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各个小岛上看到了形态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植物种类时,他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亨斯洛教授当年在课堂上所说的同种植物的不同“变种”(达尔文后来在《物种起源》中称之为“雏形种”)。因此,达尔文仔细采集了这些植物标本,并把它们的确切产地以及采集日期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十多年后,这些植物标本经他的好朋友、著名植物学家胡克 (J.D.Hooker,1817—1911) 先生研究,证实了达尔文最初的猜想。相形之下,达尔文采集各个小岛上的地雀标本时,就没有做同样详细的标记,以至于后来鸟类学家古尔德 (J.Gould,1804—1881) 先生研究时,曾为缺乏确切的产地信息而大伤脑筋。因此,科恩等人写道:“委实,当达尔文最初登上加拉帕戈斯群岛时,他显然认为植物比鸟类更有趣,因此他就没有同样仔细地标记鸟类的确切产地。”
回过头来谈谈下述悖论:为什么达尔文会在植物学研究上费时多年?为什么他对植物学贡献颇多、影响深远,生前却未曾以卓越的植物学家而名世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对植物学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其祖父伊拉兹马斯(E.Darwin,1731—1802)就是英国知名植物学家并翻译过林奈 (C.von Linne,1707—1778) 的著作。
达尔文自小就喜欢植物花草,他八九岁时跟姐姐凯瑟琳的一张合影,手里就捧着一盆花;十来岁时他就帮助父亲打理后花园里的牡丹。他 15 岁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医时,虽然不感兴趣且中途退学,但他对“药用植物”课,还是颇感兴趣的。在剑桥大学,他最喜欢的教授是植物学教授亨斯洛先生,并成了跟他“形影不离的人”。
在亨斯洛教授的植物学课程里,他不仅学习了植物的分类与解剖知识,而且有机会熟悉了亨斯洛教授植物标本室的众多植物压制标本。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仅在环球科考中为自己和亨斯洛教授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而且早在跟随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 (A.Sedgwick,1785—1873) 去北威尔士进行地质考察时,就曾为亨斯洛教授采集过那里的沙地紫罗兰标本 —— 这也是记载中达尔文最早为植物标本室采集的标本。除了他的上述经历之外,至少有以下三大因素使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情有独钟。
首先,跟达尔文的所有研究一样,他的植物学研究,旨在为他的伟大理论 —— 物种可变性以及自然选择机制提供证据。达尔文研究了从藤壶、蚯蚓到蜜蜂、甲虫等非常不起眼的无脊椎动物,也研究了家鸽、家犬、马、牛、羊等人们熟视无睹的家养动物,还研究了许许多多珍奇有趣的植物,但所有这些研究,原本都是为他计划中要撰写的那本有关物种的“大书”服务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半路杀出了个华莱士(A.R.Wallace,1823—1913),致使他的原计划中途“流产”。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无数次地向读者道歉,限于篇幅,他无法详细陈述支持他物种理论的大量证据,并期望读者对他“论述的准确性给予一定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的所有著作,都是为了“补偿”读者的信任而写的。比如,《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是对其《物种起源》书末“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那句名言(“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从中得到启迪”)以及第四章里“性选择”一节的补充;而《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的主旨,在《物种起源》里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然而我怀疑,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永久地自行繁殖。”更有甚者,达尔文的最后一本书《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在《物种起源》全书结尾处仅以 9 个字闪亮登场:“蠕虫爬过湿润的土地”。因此,我一向有个私见:若想真正读懂《物种起源》,真得通读达尔文的全部著述方可。
其次,达尔文是天生的博物学家,从小就有收集的癖好,终生乐此不疲,如醉如痴。从矿物、化石到甲虫、水母、藤壶等,无所不收,自然不会放过美丽可人的花草植物。
事实上,他的私宅党豪思 (Downe House), 除了拥有著名的英式花园之外,还有温室花房;真可谓“谈笑有鸿儒”,放眼皆花蔬。达尔文与妻子爱玛(Emma Darwin,1808—1896)都是爱花之人,经常相伴去观赏“唐庄”(Downe)南郊的兰花坞(Orchid Bank);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首次邂逅食虫植物茅膏菜。
此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达尔文的朋友圈中,很多人是植物学家、园艺师、育种家、植物采集者和收藏家,包括剑桥大学的良师益友亨斯洛教授、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胡克、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家格雷(Asa Gray,1810—1888),等等。
博物学研究属于兴趣驱动型研究,而达尔文又是典型的有闲阶级绅士科学家,他在这一植物学“票圈”里找到了知音,并在与他们的交往和切磋中不断增长知识、扩展兴趣,得以在植物学研究方面越钻越深、越走越远。因此,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是出自真爱,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陈:“在我一生中,兰科植物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乐趣”“在我整个科学生涯中,没有任何发现带给我的满足,堪比对异形花柱结构的认识”……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不仅为达尔文生物演化论提供了大量证据,而且与其他生物类群的研究相比起来,更适合他的工作习惯、研究方式和实验手段。除了讨论本能的一章与讨论地质学的两章以外,《物种起源》中所提及的植物学证据俯拾皆是。
达尔文见微知著的观察能力,历来为人称道,他总是能见人之所未见,人们熟视无睹的许多东西,他会反复仔细观察,并能迅速捕捉到它们的重要性。他还是一位极为聪明、极具创造精神的实验者,在实验设备简陋的 19 世纪(光学显微镜刚刚问世),他即开始设计了许多看似十分简单却非常有效的实验,获得了相当可靠的实验结果。
达尔文在环球科考途中染上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在他归国后折磨其余生,严重时往往生不如死,大大限制了他野外工作的可能性,其后几十年的研究与写作基本上都是在党豪思完成的。植物相对比较容易培育,且固着不动,因而非常适合达尔文基本上足不出户的工作习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他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多地转向植物。
因而,了解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他的生物演化论,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机巧的实验技能。可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生物学家与科学史家们并未把达尔文视为植物学家呢?与其说是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被他的生物演化论盛誉遮蔽了的话,毋宁说是他的植物学研究太超前了。如果说孟德尔 (G.J.Mendel, 1822—1884) 的遗传学研究超前了几十年的话,那么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至少超前了 100 年!
达尔文时代及其后的几十年间,植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解剖方面,处于生物分类系统学的所谓“阿尔法阶段”生物系统分类学的阿尔法阶段,是指生物系统分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通常只是属种的形态描述和普通性状对比、一般的归类,以利鉴定与检索,缺乏演化系统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他的朋友胡克与格雷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植物分类学家。而达尔文的植物学著作,主要是从生物演化的角度,审视植物在自然选择压力下,如何演化出适应环境的各种机制(具体体现于植物结构和器官上),比如《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植物的运动本领》《食虫植物》。抑或是探究物种形成的过程与机理,从变种(或雏形种)到新物种的衍变,即种化(speciation),以支持他的物种可变、万物共祖的理论,比如《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
这些研究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生物学中现代综合系统学派的兴起,才获得植物学家们的充分理解和普遍重视。1950 年美国植物遗传学家斯特宾斯(G.L.Stebbins,1906—2000)的名著《植物的变异与演化》问世,使得困扰达尔文的很多问题,在新达尔文主义框架中迎刃而解。
随后的 20 世纪下半叶,新学科演化植物学诞生,给 100 年前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然而,他的三本植物繁殖生物学著作,还要等待一些时日,直到植物生态学的建立,方能得以复兴。换言之,达尔文如此地先知先觉,他的植物学家桂冠,要等到他的贡献被人们充分理解时方有可能。
近几十年来,达尔文的植物学著作是除《物种起源》外,最广为阅读的。尤其是他的三本植物繁殖生物学著作,启发了很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新的研究项目,成为演化生态学或植物生态学领域的经典文献。这些既说明了达尔文研究工作的坚实透彻、经得住时间考验,也显示了他学术思想的前瞻性。《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堪称经典中之经典,不仅成为现代植物繁殖生物学的奠基石,而且为演化生态学中的协同进化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和范例。
二
达尔文自称,《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是他“近 37 年来极感兴趣的课题”,为此他收集过大量的观察材料,并设计了很多简单但巧妙的实验。在长达 11 年的实验过程中,曾起用他好几个孩子做他的“助研”,所用实验植物多达 60 余种。
他使用人工控制的授粉方法,在众多植物物种之间,观察和比较异花受精与自花受精所产出的不同后代在生长以及性状等方面的差异,指出了自花受精所带来的近亲繁殖,会对后代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即现在所谓的“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 现象]。该书于 1876 年由他的出版商默里(J.Murray,1808—1892)出版,被达尔文视为他 1862 年《论不列颠与外国兰花植物借助昆虫受精之技巧》(又译为《兰科植物的受精》) 的姊妹篇。
植物中从杂交到自交的过渡,是最为常见的演化现象之一。尽管如此,在被子植物中只有大约 10%~15% 的种类是以自交为主的。达尔文在《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中,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并用实验结果证明自花受精是有害的,而异花受精则是有益的。
后者在植株大小、生命力、种子发芽率以及植株结实力等方面,均比前者具有强大优势。此外,他还注意到许多物种都有阻止自花受精的各种机制,最简单的办法是雌雄异株,让它们“两地分居”。即便雌雄同株,有些植株上的单性雄花与雌花的成熟期是错开的,以至于“牛郎织女”不能相遇。
现在我们知道,植物还有其他一些窍门来阻挡自交的成功,比如,同一植株上的花粉含有化学阻挡层,致使不能为其胚珠受精。达尔文书中称为“自交不孕的原因”,即现在所谓的“自交不亲和性”。
一方面,达尔文明白自花受精在交配成本上相对低廉,“近水楼台先得月”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自交策略,在交配对象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适应意义。它比较容易确保交配成功,使物种迅速占领适宜生境,实现群体扩张。在短期内,自花受精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从长远来看,异花受精却有增加个体杂合度的优势,使其更容易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降低死亡和灭绝的概率,而且杂交后代的生命力也比自交后代的生命力更为强盛。不过,由于达尔文缺乏遗传学方面的知识,他无法真正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
那么,为什么植物界依然存在相当多的自花受精类型呢?首先,自花受精植物在授粉率上比异花受精植物有 50% 的优势,它们不仅能给自己授粉,也可以给异花受精植物授粉。
其次,自花授粉无须像异花授粉那样依赖传媒。从种群遗传学家的角度来看,在基因传递上,自花受精比异花受精有 3/2 的优势:自花受精植物在其种子里传递两份基因,而异花受精植物只传递了一份。这是最简单不过的算术问题。
另一方面,达尔文有关异花受精植物有着长远优势的结论,也得到了现代系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美国植物遗传学家斯特宾斯教授的支持。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时,有幸听过斯特宾斯教授的课,他有一次课,曾专门讲解“杂交是否必要?”他老人家指出,杂交虽然对传宗接代并非必要,然而它对生物多样性来说,却无比美妙!他指出,从生物演化上说,自交是“死胡同”。
在植物界,杂交向自交的过渡是不可逆的,自交类群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很差,因而遭受灭绝的概率极高。因此,尽管自交类群在植物演化史上曾多次重复出现,然而每每总是“短命”的(盖因其灭绝率很高),这也是为什么杂交类群支系在自然界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当然,聆听这些大家讲课的最为愉悦之处,是有机会听到一些有趣的八卦和“戏说”。斯特宾斯教授在课上特别指出,达尔文对植物繁殖生物学的痴迷,尤其是对杂交的兴趣,很可能缘于其一生的切肤之痛。达尔文深受“近交衰退”之苦: 他与舅舅的女儿(表姐)爱玛结婚后,共生育了 10 个子女,其中 3 人夭折,3 人终身不育。在他研究了植物的自交不孕机制之后,曾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学现象之一,植物真聪明啊……
(苗德岁,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摘自《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英)达尔文 著,萧辅、季道藩、刘祖洞 译,刘祖洞 一校,陈心启 二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9 月出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学元典 (ID:kexueyuandian),作者:苗德岁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