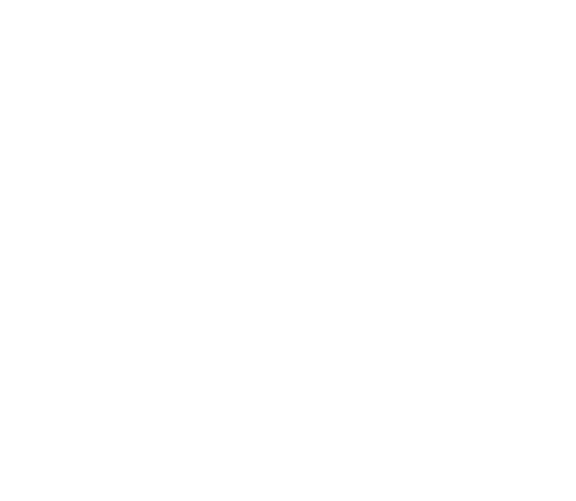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星际拓荒》:宇宙浪漫旅
- 触乐
2023-07-23 12:0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触乐 (ID:chuappgame),作者:肖达明(热灰)
我知道我随时可以故地重游。
大尺度旅行
在科幻小说《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中,韩国作家金草叶提供了一个既感性又合理的看法:对于人类来说,宇宙空间虽然无穷大,但受限于我们移动的速度,宇宙中的绝大部分区域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意义。我们生活的极限位于高空万米左右 —— 那是民航客机所能达到的位置。
然而,有大量的科幻小说和电影尝试描述星际旅行,利用想象力来填补空缺,在太空歌剧类型的作品中,我们还能见到类似银河帝国般的跨星系人类文明圈,人口数量以万亿计,奉行某种意义上的封建王权政体,以光年为距离继续地缘政治游戏。
任何事情,一旦其赖以发生的时空尺度发生畸变,自身的性质也会变化。就拿星际旅行来说吧,星际尺度的旅行幻想通常十分怪异,很难唤起具体的感官体验 —— 不像在卧铺列车上听着铁轨的震动,不像透过舷窗看到白云构成的茫茫原野,不像在深夜巴士上,前后摇晃着疲惫的身体,看着潮湿的街道在眼角闪烁、蜿蜒。
用来展示星际长途旅行的方式,通常是在飞船前方制造出一片翘曲的真空,在舷窗内,船员会看到无数色彩斑斓的光芒于隧道中旋转,并极速向后退却,化作无数条光带。更符合科学的情况是,船员们会被勒令躺进冷冻舱,对旅途的过程无知无觉,故事发生在他们醒来以后,这类星际探索故事常常包括一个枯燥无味的行程和一个怪异恐怖的目的地。
一旦牵涉到宇宙,尺度总是一个需要强调的卖点。当开发商向玩家介绍太空题材游戏时,频繁列举可怕的数量级 —— 数千颗可供探索、搭配独特地貌的行星,整个银河系任君遨游,乃至以无限作为尺度,试图生成整个宇宙。
在我印象中,较早开始这种“大放厥词”的游戏是 EA 发行的《孢子》,由《模拟人生》的制作者威尔・莱特(Will Wright)开发,曾名噪一时。这款游戏曾带给我无数快乐,那些如遵循随机性定律生成的世界与生命充满荒诞与喜感,但玩家们会发现,随着时间的进展,游戏后期的乐趣陡然下降。
随着复杂度累积,设计者必须从文明的角度,而非个体血肉的角度来看待宇宙,早期的随机性玩法变得力不从心。多样性的幻觉被扯下,在这些外星生命 3 颗脑袋或 8 条腿的身躯之内,躲藏着平平无奇的人类,而且是一群被高度简化、掌握高科技的野蛮人,在《孢子》的游戏后期,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征服、改造、扩张领土。
让我们承认吧,星际尺度的战争令人心生虚无空洞之感,一遍遍提醒我们生命的无意义。我们仰望星空并心生向往,不是为了征服与杀戮,而是被一种希望抵达异域、见识奇观、超脱世俗的冲动俘获。换言之,一种旅行的冲动。
旅行时,你总会期待见到独特的风土人文,哪怕这些事物外观朴素,哪怕它只是一块石头、一栋老宅、一把椅子,重要的是流淌在其表面的独特历史,重要的是时间雕琢它们的特殊方式。我讨厌开放世界中的随机性,我讨厌开发者向玩家吹嘘他们构造的世界使用即时生成系统,制造出巨大的可玩沙盘。
“大尺度”意味着空泛的承诺。《群星》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它拥有令科幻迷狂喜的众多元素 —— 精雕细琢的科幻事件、尺度浩瀚的宇宙、不同种类的文明形式。但在游戏后期,无尽的战火还是让我精疲力竭。在巨大的尺度和高远的视角下,随着操作复杂度的堆叠,一切行为都变得极为笨重,玩家不再有耐心应对琐碎的事件,玩法趋于野蛮,高等智能生命如中世纪的封臣一般相互倾轧。
何时我们会记起,轻盈是一种美德?何时我们会明白,当你背负太多,旅程就会变成一场徭役?何时,我们能够体会一场真正令人心满意足的星际之旅?
嵌套
2019 年 5 月,莫比乌斯工作室发布了天马行空的科幻题材动作冒险游戏《星际拓荒》(Outer Wilds),并斩获了当年的金摇杆最佳独立游戏奖,和 2020 年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 Game Awards)最佳游戏奖。直至目前,它仍然是我心中最好的星际旅行游戏。
在《星际拓荒》中,莫比乌斯工作室完成了一件创举。要描述这一创举,我需要列出以下几件事实。
首先,游戏的故事尺度极大,带有一丝黄金时代的思辨与浪漫,它试图讲述宇宙的起源与未来。在故事的背景里,名为“挪麦人”的星际游牧民族,收到来自宇宙彼端的奇特讯号,这一讯号的年龄比宇宙本身更古老,发射该讯号的目标被称作“宇宙之眼”。挪麦人历经艰辛,只为揭示“宇宙之眼”的意图。
其次,游戏的世界尺度适中,玩家的活动严格限制在一个虚构的太阳系内,这个太阳系每 22 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超新星爆炸,并被重置时间。可探索环境包括 5 个行星、一系列自然卫星与人造天体残骸,全部经过精心设计。即便是具有随机性的景观,也与世界观设定紧密结合(宏量子效应),作为奇观和谜题的一部分,随机性亦完全服务于故事的需求。
第三,游戏的视角尺度极小,它以第一人称方式进行。在游戏中,玩家扮演太阳系内的原生种族 —— 哈斯人的一名宇航员,你的任务是探索已经灭绝的挪麦人留下的遗产,并在挪麦人工作的基础上,揭开“宇宙之眼”的秘密。
这是一个美妙的尺度嵌套,主题之宏大与视野之狭小,要求制作组具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技艺,一种极限取巧的意识。我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上述 3 点 —— 在游戏中,玩家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宇宙尽头(无论是空间意义上,还是时间意义上)的探险家,一个漫长冒险的最后一环,作为哈斯人,玩家将会踩着前人的脚印前行,并做出最后的终极一跃,直抵宇宙与生命的起源之谜。
用小尺度的描写来承载大尺度的事件,这种技巧的使用令人联想到卡通,但在制作组的呈现下,它无损于游戏中宇宙的魅力。宇宙依然浩瀚,这场逐日之旅依然具有壮丽史诗的况味。只是由于故事结构上趋于极限的取巧,主人公被置于这场史诗的最后一个章节,玩家能在探索、继承前人遗产的过程中直抵高潮。
不论是故事本身,还是视觉体验,你都能感到这种奇特的空间与时间的尺度嵌套,你能在视觉上明显感到不同层级的事物紧密联结,其比例尺的差异减小得恰到好处。要理解这件事情,一个非常直观的方式是打开游戏,并经历游戏中的第一件事情 ——“醒来”。
《星际拓荒》故事始于你深深的呼吸,醒来,发现自己坐在一座温暖的篝火旁。你正顺着木架结构的高塔凝望天空,一颗翡翠绿色的巨型行星高据头顶,一串神秘的电火花在它附近闪耀隐没,以此为前景,你能看到后面那片静谧的星空,大大小小的恒星点缀其中。同一时刻,你又能清晰地感到身边的蝉鸣、树林中的风、篝火的火焰轻轻摇曳,深谷里木屋窗户漏出的暖黄色灯光,你的呼吸逐渐平稳,你捡起一根树枝,怡然自在地烤上一串棉花糖。
你会注意到这个场景的奇特之处 —— 篝火、木屋与树林,这些元素散发着拓荒时代的怀旧气息,一座火箭发射塔就在你视野的中心,却完全是木制结构搭建的,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观火台 —— 游戏中的人物也会自嘲说它随时会被火灾烧掉。发射台上的太空船由木头和少量金属矿石缝合而成,却是你能在当地找到的最“科幻”的东西。
小尺度的事物近在眼前,而巨大的天体悬于头顶,触手可及,像活物一样移动。当你把信号镜对准它们,你能听到其他探险队员在那些星星上演奏班卓琴、口琴、长笛等乐器,那种亲密的氛围就仿佛他们住在你家隔壁而不是在另一颗天体上。这一切在暗示你,游戏里的空间与时间,其结构相比现实中的宇宙排列得更加致密。
正如标题“Outer Wilds”所暗示的那样,游戏里的星际空间有着荒野的气息,它原始而生机勃勃,遥远却并非触不可及,在这样的星际空间活动,需要的不是工业革命,而是匠人与探险家的浪漫精神。也像那个时代的旅行一样,你将单枪匹马,历经颠簸与奇险。
行星浪漫旅
我不会忘记 3 年前第一次游玩《星际拓荒》时的体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我化身为一个年轻的哈斯人,一种长有 4 只眼睛、蓝色皮肤,性格温柔诙谐的类人生物。这些生物丑得可怜,看上去人畜无害 —— 我在整个城里游逛,看到唯一带点棱角的东西是一柄伐木斧(全村独此一把)。
根据故事的设定,在遥远的过去,我的先祖还是木炉星上一滩水洼里的两栖生物,而挪麦人来到这个太阳系,试图揭开宇宙之眼的秘密,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他们需要在木炉星上开采大量矿石。
和你相比,他们宛若神明,可当他们掀开一块石头,发现那摊水洼,发现你的祖先在里面轻轻游弋时,他们没有说“我来,我见,我征服”,也没有说“毁灭你,与你何干”。
他们只是轻轻放下石头,告诫彼此要尽量减少开采矿石,并相信:“许多年后,他们会发展他们的文明,他们也会探索整片宇宙,见识我们见过的风景,那时,他们会需要这些宝贵的矿石,那时,也许他们会加入我们。”
在《星际拓荒》中,这种温柔的笔触随处可见,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暴力。游戏的主题就是探索与发现,也聚焦于此。你将亲自驾驶飞船,看着日月星辰在舷窗外旋转,你将掠过行星表面的狂风,穿过流星火雨,潜入浩瀚深海,捕获量子卫星。一切都是所见即所得,没有高层级的复杂操作,没有喧嚣的火光。你将踏上名副其实的旅程,并满足自己的好奇。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探险经历之一,是走在碎空星的地表下那些摇摇欲坠的悬空石上,看着这颗行星逐渐被自身核心所吞噬。就在我的脚下,一颗黑洞正在源源不断地扩张体积,它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野兽,将行星的骨肉大口大口地咬进嘴里,又像一个巨大的眼珠,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
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悬空城中步履薄冰;不得不在启动喷射背包跳跃时留心脚下的落点是否坚固;不得不在重力水晶的保护下轻挪慢走,穿越一片片倒挂的极低冰川 —— 黑洞就像黑色的太阳悬在头顶。可是突然之间,我失手了,重力颠倒,天空变回黑暗的大地,我绝望地下坠,徒劳摆动四肢,但没有什么可以保护我,引力像绳子一般捆住我,随着不断靠近黑洞,眼前的一切都被拉长、变得凹陷,最终是我自己 —— 我被整个吞掉,你被压扁,失去一切,而游戏会在死亡的白噪音中结束。
等等,等等…… 我心惊胆战,睁开眼睛,却看见一片明亮、温暖的光挤在身后,我已被黑洞吞下,却没有被压碎,原来它是一个隧道,而隧道的尽头还有另一个洞,那是一个光明四射的“白洞”。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可“白洞站”就在不远处。用喷射背包轻轻一推,就回到了有氧气、有重力的地方,来自几万年前的一条留言告诉我:“吓坏了吧?不用泄气,我知道你可能会落进黑洞,所以我们建造了白洞站,利用跃迁技术帮助你返回。”
这趟旅程充满惊险和难以逾越的困难,有时候几乎令人沮丧,但玩家总能得到答案,得到鼓励。当你身处绝境,总有人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不要害怕,“我们会帮助你返回”。
每当我在游戏中感到孤独,我总是能在下一个瞬间得到安慰,总能从险境中平安返回,或者带着知识重新面对挑战。
“返回”是《星际拓荒》故事的一个关键词,“返回”不是旅程的终结,恰恰是延续。每 22 分钟,宇宙会被毁灭,玩家却会带着记忆重返起点,继续你的冒险。“返回”是故事的情感主题 —— 你的根基始终呼唤着你,当你前路茫茫,迷踪失路时,直面内心深处的渴望会引导你回到那条你重视的道路上,你心灵的故乡不在身后,它的灯光闪烁在前方。
如游牧民族一般在星空中旅行的挪麦人,有一天接收到一个信号,根据测量,发出信号的那个对象 —— 被称作宇宙之眼 —— 竟然比宇宙本身更加古老。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决定追随这个信号,他们决定找到它,因为驱动这个种族的核心动力是永无止境的好奇心,
在追逐宇宙之眼的艰辛中,他们失去了飞船、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与同族的联系,如一叶孤舟,搁浅在小小的太阳系。
他们有两个选择。一种是重新建造一艘飞船,放弃计划,逃之夭夭,试图忘掉一切。而另一种选择是坚持留在太阳系,接受飞船已经毁灭、族人无法团聚的命运,从头开始,一代又一代繁衍,一代又一代营造,直到他们的后代重新登上天空,直到他们找到答案为止。
在故事中,直到种族全灭的尽头,直到最初抵达太阳系的元老已经全部死去,挪麦人的后代依然没有动摇过,一直执行计划直到最后一刻。他们的失败在于没能活着见到真相。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几万年过去之后,当初在小水洼里游弋的两栖动物进化至今,并已经具备了智慧,开始用木头、矿石、黏糊糊的树液建造飞船。
“你”来了,他们为你留下的矿石全都发挥了作用。你搭上飞船,来到他们失败的末尾,引擎点火,你直入星空,“返回”一段被掩埋的过往。在这段旅程中,你了解他们的爱、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执著、他们的幽默,他们彼此打情骂俏的方式,他们探问星空的话语,他们夸张到近乎疯狂的伟大计划。现在,一切全部来到你的肩上,你会继续吗?为什么不呢?你还能找到更浪漫的事情去做吗?还有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时看到的风景,更加辽阔的风光吗?
我知道我会继续那个计划,我必须重新得到答案,我必须苏醒在那片美丽的星空下,坐在篝火旁,烤糊我的棉花糖。我必须前往深巨星,突破它的气态薄膜,穿越星球级的龙卷风,并落到孤岛上,看着另一个探险家 —— 加布罗躺在吊床上,在惊涛骇浪中优哉游哉地吹着笛子,并毫不在意地被龙卷风甩到真空中,于失重的状态下继续演奏音乐,仿佛整个星球只是他屁股底下的一张秋千。
灵魂共鸣
你试没试过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你儿时住过的地方,小时候一切显得巨大的东西,都会突然变得极为矮小。数年之后,当我重返《星际拓荒》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微缩的太阳系有多么触手可及,半分钟之内,我能从木炉星启动飞船去往任何地方 —— 深巨星、沙漏双星、碎空星、黑棘星。可是,3 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却震惊于它的宏大。
你会见到由龙卷风支撑起的浑浊天幕,你会见到双星系统如沙漏一般来回转移着行星物质,在黑棘星,你会发现每个异次元种子都是外小内大,进入其中就会进入另一个空间,你甚至会在种子的内部找到种子的本体,进入无尽嵌套的异次元空间。你能想象初见这一切时的惊愕吗?当恒星在你眼前发生超新星爆炸,蓝色火光将一切蒸发,你会听到心跳,你会忘记呼吸。
在《星际拓荒》的世界,宇宙并不想要吓唬你,群星并不心怀恶意。而当你熟悉它们的每个角落,也并不意味着你会觉得无聊,你依然觉得震撼,只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发生在你自己的心中,你被提醒,在彼时彼刻,你曾经获得勇气,也曾经这般好奇,你变得充实,你也变得宏大,故地重游只是在提醒你回想那一切,并找到力量。你想到张伯伦的诗 ——
仅在昨天,我认为我自己只是碎片,无韵律地在生命的穹苍中颤抖。而现在我知道,我就是那穹苍,一切生命都是在我里面有韵律地转动的碎片。
去年我在 B 市工作,给一个科幻手游写世界观,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直到那时,人类之间,人与外星人之间的厮杀仍望不到尽头。一颗又一颗行星被摧毁,可女人们依然性感,那是我写的;我写,引爆一颗恒星只是战略中微不足道的一步,整个星系都已被炸成空洞,随处都是穿着暴露的女性和恒星的残骸 —— 致命、虚无的黑洞。
在给手游写作世界观的一年,我对电子游戏逐渐感到厌倦。不断接触软色情与妄图用故事合理化暴力,让我身心俱疲,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荷尔蒙的年轻玩家,作为玩家,我已开始衰老,不断受挫,需要慰藉而非对抗。在写作世界观的时候,我开始厌恶游戏,开始讨厌原本热爱的科幻题材,离开那家游戏公司后,我有一种刑满释放的舒畅。
重返《星际拓荒》是一种自我疗愈。挪麦人作为具有星际长途跃迁能力,时空回溯能力的神级文明,却几乎没有开发过任何武器。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遗产的哈斯人,除了砍树用的斧头,也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武器的东西。我承认,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但相信暴力能够创造伟大的星际文明,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加黑暗,充满偏见的理想主义?
也许游戏就是游戏,游戏是用来娱乐的,但是游戏也可以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当我在网上游逛,寻找与《星际拓荒》有关的一切时。我在游戏网站 Gameluster 上找到一篇令我十分动容的文章,文章的主人公 Clare FitzPatrick 于 2021 年确诊癌症,陷入人生中的最低谷,在长达 6 个月骨肉烧灼的化疗,熬过极度抑郁的大半年时光后,他开始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
作为心理疗愈的一部分,他开始玩《星际拓荒》,对于他来说,不论是他在现实中经受的折磨,还是在游戏中遭遇的挫折,都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 —— 是的,这款游戏很难,我听过很多玩家因为迷茫和挫败而放弃体验。
每次在篝火边睁开眼睛,都会让 Clare 想到自己的病,想到自己深陷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面对一些谜题,他不得不在网上寻求帮助,才能获得答案。就像他必须向亲人与朋友求援,才能熬过那段艰难的时光,并逐渐迎来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他写道:
“朋友的爱,家人的关心,让我的病情得以缓解。哈斯人的支持,挪麦人的遗志,助我找到宇宙之眼。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有那么多人无法活下来,我每天都在想他们。每天,当我看到肚子上的伤疤,当我因为化疗而导致的永久性关节炎而手腿疼痛时。我都会记起医学创新的进步,治疗的进步,很多人没能活着见证这一切,但他们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当演职员列表开始滚动,钢琴声渐渐淡出,而大提琴开始嗡鸣,我想起了这一点。我想起这一切并开始哭泣,我们可以从宇宙尽头的小小哈斯宇航员身上学到许多,他背负知识的重担,一次又一次地克服每一个障碍,走向挪麦人用生命开拓的通向宇宙之眼的道路。而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此刻融为一体,亲密无间。”
我也记得那种想哭的冲动,我也记得自己如何依依不舍地盯着演职员列表滚动,如何一遍遍在手机里循环播放游戏里的原创音乐,并给音乐下的每一个评论点赞,恨不得穿过屏幕去拥抱他们。我不敢奢望这种体验每天都有,我不会奢求睁开眼时,头顶总是一片璀璨的星空。但知道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知道我可以随时故地重游,知道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各种人,在不同时刻、同一情形下落泪,带给我一种深刻的慰藉。我还能感受,我还能一次次被触动心弦。
当我无数次在木炉星上的篝火旁苏醒时,我看到一根隐形的、巨大的纽带。它连接着我、哈斯人、挪麦人、宇宙、开发团队、以及其他的玩家,这一纽带重新定义了我,疗愈我自身的伤口,而就像里面的量子卫星一样,当你定睛注视,并终于看到那一切时,就不要轻易挪开目光,就一直注视它,抓住它,铭记它,以免它消失。因为时间会推移,你迟早会迷失在路上,原先的纽带真的可能会消失,到那时,你也许就得重新“苏醒”。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