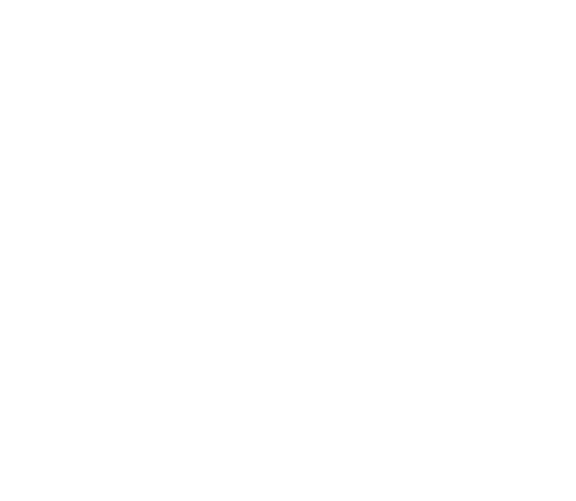一场意识理论大混战,甚至“伪科学”帽子都飞出来了
- 返朴
2023-12-30 14:2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顾凡及
意识研究领域最近热闹非凡,一场绵延 25 年的研究赌约兑现了,一个历时 5 年的对抗性研究也有了初步结果,还有 124 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把一项理论斥为“伪科学”…… 诸此种种,甚至让意识研究学界陷入乱战局面。实际上,由于究竟什么是意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甚至对意识究竟包括哪些方面都没有共识,那么,不同学者寻找全面刻画意识的指标就相当困难。身处局中的学者们也要有耐心,不急于达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统一意识理论。
撰文 | 顾凡及
这一阵,在意识研究的舞台上,耸人听闻的八卦漫天飞舞,许多本来关系不大的事件(当然也有很少的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是事关意识研究)被扯在一起,如果不清楚其脉络的人仅仅根据道听途说,真会被搞得昏头昏脑。本文试图把这些事缕缕清,以正视听。
笔者讲的是哪些事件呢?一件事是德裔美国神经科学家科赫(Christof Koch)25 年前打的赌,输给了澳大利亚哲学家查默斯(David Chalmers)。一件是邓普顿世界慈善基金会(Templeton World Charity Foundation)资助不同观点的意识理论研究者进行对抗性合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意大利裔美国神经科学家托诺尼(Tononi)和科赫为首的整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IIT)和以法国认知科学家德阿纳(Dehaene)为首的全局神经工作空间理论(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 theory,GNWT),经过 5 年对抗合作,由第三方进行检验。第三件事是一方面权威杂志《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等载文称赞了这一对抗性合作;另一方面,有 124 位意识研究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把 IIT 谴责为“伪科学”。第四件事是其实在同一把 IIT 大伞之下,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内容,而称赞和谴责的实际上又是这面大旗下的两个非常不同的内容。由此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评价为什么如此南辕北辙?两大学派研究的对象除了共同与意识有关之外,研究的究竟是意识的同一个方面?还是不同的方面?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厘清,那么上面这许多看似自相矛盾的事会把人的头脑都搞糊涂了。
四分之一世纪的赌约
第一件事最简单。2023 年 6 月在第 26 届意识科学研究协会大会(The 26th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ASSC)上,科赫对他和查默斯在 25 年前打的一场赌勉强认输,买了 5 瓶葡萄牙葡萄酒送给查默斯。
25 年前,科赫赌的是有关“主观的意识是怎样从客观的神经回路中涌现出来的”这一被查默斯称为意识的“困难问题”(hard problem),或者如他和其忘年交克里克所说的“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可以在 25 年内得到解决。现在,有人问他敢不敢再赌一把,他回答说,“我会加倍下注,从今算起 25 年是现实的,因为技术越来越好,你知道,考虑到我的年龄,我不能等更长的时间了。”[1]
事情的缘起是 1990 年,克里克和科赫在其重要论文《走向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理论》(Towards a Neuro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中声称,现在是将意识研究置于神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克里克认为,打仗要从攻击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研究意识也是一样,应该从研究脑中哪些神经活动和视知觉相关 —— 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开始。当时进行此类实验研究的一个拦路虎是当主体受到视刺激后的脑活动变化,既可能是由于视知觉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刺激变化本身引起的。
1996 年,在德国工作的希腊神经科学家洛戈塞蒂斯(Nikos K. Logothetis)利用双眼竞争,研究了当刺激不变而知觉改变时猴子脑中哪些区域的神经活动发生了变化。所谓双眼竞争就是给主体的双眼分别看两个完全不同的景象时,主体看到的并非这两个景象的融合,而是轮流看到其中之一。我们只要戴一副红蓝眼镜看周围世界,就可以体验到这一点。
类似地,他们给猴子的一只眼看太阳图案,而给另一只眼看其他物体。猴子通过扳动不同的手杆来表示自己看到了哪类图案。结果发现,在初级视皮层和次级视皮层,绝大多数细胞的发放率与知觉的反复变化无关。总体来说,只要一只眼睛有输入刺激,神经元的发放就会增强。这与猴子究竟看到了什么无关。因此一般认为 V1 对意识贡献甚微。他们又发现在对猴子下颞叶(inferior temporal,IT)皮层及上颞叶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STS)的下侧(该区域与 IT 上部相邻)进行实验记录时,只有当猴子“看到”时才有发放。
克里克对此非常兴奋,他认为这一技术已使科学家找到了研究视知觉神经相关集合的钥匙,并宣称到 20 世纪末就能发现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
作为克里克志同道合的长期合作者,科赫当然也同样兴奋。另外,像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和光遗传学等新技术的出现,使科赫在当时认为:“所有这些新技术都让我着迷。我想:用 25 年的时间去解决应该没问题。”[1] 科赫在 1998 年和查默斯打了这个赌。所以这个赌只与能否在 2023 年解决查默斯的“困难问题”有关,而与其他论点无关。要不是有位科学记者在当时把这一赌约记录了下来,他们两人可能都把这件事忘了。
就在几年前,两人都参加了邓普顿世界慈善基金会的对抗性合作计划,于是旧事重提,又把往事翻了出来,才有了上面的一幕。
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
按照科赫的定义,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就是“神经元的某种机制或事件的集合。该集合是形成某个特定知觉或体验所需要的最小集合。”[2] 请注意,当科赫在 2004 年给出这一定义时讲的是意识到“特定知觉或体验”的意识神经相关集合,它所确定的部位是比较局限的,也随其特定内容而异。后来,他和托诺尼又引申出对所有可能意识内容的意识神经相关集合的总体,并称之为全意识神经相关集合(full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3]
此外,由于定义中对“最小集合”的要求(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要求,那么把全脑都说成是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虽然也符合定义,但是就没有意义了),因此需要排除对脑涌现意识非必要的事件,例如由受试者注意或计划说话或按按钮所引起的脑中事件。为了排除这些影响,近年来发展出各种技术(例如检测眼动或瞳孔放大),无需主动报告就可以确定受试者是否意识到了某种内容,由这种“无报告范式(no‑report paradigms)”所确定的有特定内容的神经相关集合比需要报告时得到的更局限于皮层后部。[3]
研究全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不同状态的方法”(state-based approaches),这种方法是把清醒的健康受试者在不要求做任何任务而有意识时的脑活动和意识丧失时(如无梦睡眠、全身麻醉、昏迷或植物状态)的脑活动进行比较。这样得到的全意识神经相关集合往往包括额-顶叶网络,但是这里有些部分可能和受试者的警觉、注意等脑功能有关。为了排除这些因素,采用另一种“同样状态无任务范式”(within-state, no‑task paradigm),这主要是利用意识的自发波动,例如当受试者处于无快速眼动睡眠期时将其叫醒,有时受试者说是正在做梦,而有时则没有任何意识。把受试者在报告做梦或无意识前记录下来的脑电图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全意识相关神经机制主要位于包括感觉区在内的后皮层热区(posterior cortical hot zone),也就是包括皮层后部颞-顶-枕叶交界处在内的脑区,这和根据有特定内容的意识神经相关集合所得的结果在总体上吻合得相当好,因此可以把后部皮层区看作意识神经相关集合的热门候选区。[3] 这一观点笔者称之为“后脑理论”,或更无歧义,由于这是科赫和托诺尼合作的结果,而托诺尼早已因他制定了一个度量意识的指标 Φ 并冠名为“整合信息理论”而闻名,而科赫也曾称赞过这一理论是“有关意识的唯一有希望的基本理论”,因此他们的这一观点也被称为 IIT,这就造成了混淆。
一词两义:托诺尼的整合信息理论 ——Φ
托诺尼曾是诺奖得主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的长期合作者,他们曾经提出过“整体性”和“信息性”(或称“神经复杂性”)作为衡量意识程度的定量指标。虽然他们指出过“私密性”也是意识的一个基本特性,但是未能给出定量指标。托诺尼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考虑了意识更多的基本性质(其核心依然是整体性和信息性,但是却略去了“主观性”或“私密性”这一意识的根本属性),并以此作为“公理”。这些公理包括:內禀存在性(Intrinsic existence)、结构性(composition)、信息性、整体性(integration)、排他性(exclusion)。
正是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之上,托诺尼认为如果一个物理系统要有意识的话,那么这个系统就必须有和上述公理相应的性质,它应该是一个有数量极大的可能状态的统一整体,为此在有关脑区之间必须有交互作用。一旦这些脑区之间开始失去连接,或者其组成部分失去特异性,意识就会消退,这便是在深睡、麻醉或者癫痫发作时的情形。意识的程度可用该系统超越其各组成部分所含信息量的总和的信息量来度量,他们把这称为“整合信息(integrated information)”,并用符号 Φ 来表示,以度量一个系统不能被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在互不相关时所具特性的程度。他们认为可以用 Φ 值来判定系统是否有意识和意识的程度。[4] 为了区别于后脑理论,笔者在本文中称之为 Φ 理论。虽然在现在所有的文献中它们都被称为整合信息理论。
全局神经工作空间理论
法国认知神经科学家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提出的全局神经工作空间理论 [5],也以其较强的神经生物学背景而引人注目。
由于对意识仍然没有明确和普遍接受的定义,为了避免混淆,德阿纳将他的研究集中在他所谓的“进入意识(conscious access)”(受试者意识到了其所受刺激并可以向其他人报告的现象)上。很少人会否认这是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是通向更复杂形式的有意识体验的门户。
他们使用掩蔽、双眼竞争和其他方法表明,虽然刺激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但受试者的知觉却可能发生根本变化,例如从意识不到变成意识到,或正好相反,因此进入意识可以被视为唯一的变量,并可以通过实验对这一变量进行操控。然后,他们就寻找当也只有当受试者对相应刺激有“进入意识”时才会出现的脑活动模式。他们将这些模式作为进入意识的标志,并称之为“意识标记(conscious signature)”。他们发现有如下这些标记:(1)刺激诱发的脑活动大大增强,扩大到多个脑区并突然引发前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许多回路的活动;(2)脑事件相关电位中的晚成分 P3 突然增强;(3)在晚期突然爆发高频振荡;(4)跨脑区域活动的同步化。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他总结说:
“在给刺激后大约 300 毫秒左右开始进入有意识状态,在此期间,脑的额区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接受感觉输入,但是这些区域也以相反的方向自上而下发送大量投射到分布很广的许多区域。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个由许多同步活动的区域构成的脑网络,其各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意识标记。”
“当有有意识的知觉时,神经元群以协调的方式开始发放,首先是在一些局部的特定区域,然后蔓延到皮层的广大范围。最终,它们侵入到许多前额叶和顶叶脑区,同时与前面的感觉区保持紧密同步。正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脑网络,有意识觉知也似乎由此产生。”[5]
据此,他们提出了一种“全局神经工作空间假说”(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 hypothesis):
意识是一种在全脑范围里的信息共享。人脑中有高效的长距离网络,特别是在前额叶皮层,以选择相关信息并将其扩播到整个脑。意识是一种演化装置,它使我们能够注意某个信息并在这一扩播系统中保持活跃。一旦这个信息被意识到了,根据我们当时的目标,它可以被灵活地传送到其他区域。因此,我们就可以叫出它的名称,对此进行评估,记住它,或者用它来规划未来。 [5]
和科赫与托诺尼的“后脑理论”相反,在德阿纳的“全局神经工作空间”理论中前脑扮演着重要作用,笔者在本文中把它称为“前脑理论”。
一对对抗性合作
在邓普顿世界慈善基金会所资助的对抗性合作中,牵涉到 20 种左右的意识理论。科赫 / 托诺尼学派和德阿纳学派以其较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和明显不同的观点脱颖而出:前者强调后脑的作用,而后者则强调前脑的作用,这样两者看起来似乎有更明确的可比性。
基金会资助了六个独立实验室遵照双方预先商定的方案,并分别用功能性核磁共振、脑磁图和皮层电图技术对 250 名受试者测量其脑活动,以检验这两种理论对他们共同认同的两个实验方案中第一个方案的不同预测,双方自己并不参加实验。这些结果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结果对这两种理论既有支持之处,又不完全匹配。这些结果同时在 ASSC‘23 年会上公布了,难怪人们把 25 年前的一场打赌和对两大派理论的对比进行评判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了。
参与该检验的德国神经科学家梅洛妮(Lucia Melloni)认为,“关于 IIT,我们确实观察到,后皮层脑区持续有信息。”但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 IIT 所预测的脑区之间有持续的同步活动。
至于 GNWT,研究人员发现,意识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在前额叶皮层中表现出来,但并非一切意识活动都可以在此有所反映。此外,实验发现只有体验开始时才有信息扩布的证据,但未能发现在体验结束时也有扩布。
总体而言,IIT 稍优。不过梅洛妮强调说:“但这并不意味着 IIT 全对,而 GNWT 全错。”这不过意味着两派的支持者都需要根据新的证据重新思考他们的理论。
人们正期待着 2024 年年会上宣布第二个方案的检验结果。以前在科学上很少这种有点像体育比赛的同台竞技,这自然引起了媒体的兴趣,甚至在像《科学》[6] 和《自然》[1] 这样的权威杂志上都有报道。不过报道中称这两派理论为“领先的”(leading)一词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就 IIT 受到了实证检验的说法被人大做文章。
124 名意识研究专家联名公开信指责 IIT 为伪科学 [7]
IIT 和 GNWT 受到举世瞩目,也为盛名所累。124 位意识研究者,其中包括巴尔斯(Bernard J. Baars)、丹纳特(Daniel C. Dennett)和丘奇兰(Patricia S. Churchland)等著名学者,联名发布一封公开信,指责《科学》《自然》等媒体做了不实报道,并指责 IIT 是伪科学。但是信中通篇没有谈到这一对抗性合作的关键主题 —— 前、后脑之争,而是抓住了和托诺尼的 Φ 值有关的问题全盘否定。
笔者读后不禁会想,签署联名信的专家不至于连后脑理论和 Φ 假设的区别也看不出来吧,以笔者小人之心,不免怀疑这或许是有科学本身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吧!不过由于 IIT 并未将后脑理论与 Φ 理论做过切割,两者都顶着 IIT 的名义,提出者相同,也不能说是代人受过,这又怨得谁来!
笔者点评
意识研究上的这一场大混战,真可谓好戏连台,令人目不暇接。如果不追根溯源,真有点令人不知所措。笔者作为一个长期对此感兴趣的旁观者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得之见,和读者讨论。
首先,是有关科赫和查默斯之争。关于科赫愿意双倍下注在今后 25 年内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先要讲清楚是指解决意识的神经相关集合的问题呢,还是解决查默斯的困难问题。科赫似乎把这两个问题认为是同一个问题。
笔者则不敢苟同。因为前者是指探讨涌现意识的最小神经事件集合,或者说探讨人脑涌现意识的必要条件,注意这里讲的是“相关”,而不是“因果”,这在今后 25 年内是有可能解决的(不过笔者不敢打赌);而查默斯所说的“困难问题”则是要想阐明脑这个物理系统怎样产生主观意识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 [8]。其理由是意识在像人脑这样一个极复杂的多层次系统顶层涌现出来的一种不可还原的性质,其不可还原性并非是因为处于多层次系统的最底层(也有人虽然承认意识的不可还原性,但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循环因果关系带来的结果,而错误地认为意识也像电荷一样是万物普有的一种基本性质,从而陷入到泛灵论的泥沼之中),从而无法进一步往下还原。而是因为这种复杂系统所遵从的因果关系不再是线性因果链,而是循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各个层次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双向的相互作用【埃德尔曼把其称之为“复馈(reentry)”,认为这是产生意识的必要因素】,也就是说互为因果。意识既然不可还原,因此就不能问“怎样”产生的问题,而只能研究其涌现所需要的条件和它所具有的性质。
因此,在笔者看来查默斯的“困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在人们没能认识循环因果关系的规律之前,人们就无法回答“困难问题”。所以如果科赫打赌的是在今后 25 年内解决意识的困难问题,那么他得再准备 10 瓶葡萄酒。
其次,科赫 / 托诺尼和德阿纳的对抗性合作实际上是关公战秦琼。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针锋相对,前者强调后脑,后者强调前脑;但是他们实质上研究的是意识这把大伞的不同方面,前者是研究无报告的全意识神经相关集合,其前提是要竭力排除注意、计划等因素,而后者基于进入意识,注意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而无法排除。而有关注意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至今并无定论。
第三,虽然 124 人公开信故意回避了在对抗性合作中的 IIT 实际上是指后脑理论,而和 Φ 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对对抗性合作的批评就像是枪打稻草人,但是他们对 Φ 理论的批评却有其合理之处。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且不说像意识这样复杂的对象能不能用公理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即使可以,在托诺尼的 5 条公理中也故意丢掉了对意识来说最关键的“主观性”,因此由这样不完备的公理系统推导出来的 Φ 指标,充其量也只能度量意识作为神经系统超越其各组成部分所含信息量的总和的信息量这一个方面,而非意识本身。或许用这个指标在某些场合下也能作为判断意识程度的参考(例如当深睡和癫痫大发作时,大脑皮层各部分的活动高度同步,缺乏特异性和信息性,其 Φ 值也低,而此时的意识程度也很低),但是绝不能用以判断对象之是否有意识,否则就会得出任何内部有相互作用的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的荒谬结论。从这一点上来说,公开信对 Φ 理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由此说其为伪科学则是过了。香农(Shannon)的信息量定义刻画了信息传输减少了发送者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刻画信息对接收者的意义或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香农的信息论是伪科学。当然香农审慎地仅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信息传输的问题上,并没有说他的理论也适用于信息处理,甚至发送者的状态变化对接收者的意义问题上,笔者也并非说这两个意识理论就像信息论一样重要。
第四,笔者认为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假设对于进入意识标记的解释没问题,但对他的假设是否也能够解释意识或者即使只是进入意识本身持怀疑态度。[9] 其主要理由如下:
(1)“进入意识标记”并不是“进入意识”本身,就像某人的签名并不就是他自己一样。你不能简单地用相应标记的机制来解释事物本身的机制。对标记的解释可能会对其所有者的解释给出一些提示,但并不能给出后者的确切解释。严格地说,德阿纳的研究只是表明,如果主体有进入意识,那么他 / 她的大脑中就有这样的标记,但反之并不一定成立。另外,尽管进入意识是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并非是意识全体。例如不接收任何刺激时的胡思乱想,甚至“意守丹田,内心一片空明”显然还是有意识的,但是并非“进入意识”。
(2)除了用受试者的主观报告来判断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什么之外,德阿纳的工作并没有触及意识的主观性问题。他所有的实验和理论都是基于客观事实。他使用客观标记来取代主观的进入意识。因此,即使他的假设阐明了这些标记是如何起源于一些特殊的脑活动模式的机制,并且即使他的说法可以扩展到进入意识本身的机制,他的理论最多也就像关于立体视觉的双眼视差理论。后者确实解释了立体视觉在哪种情况下会出现,就像 3D 电影已经证明了的那样,但是它仍然不能解释我们“怎样”能够具有这样的主观体验特性。
第五,后脑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采用“无报告”范式的研究方法,但是也有科学家根据一些报道称在采用这种方法时,也能在前额叶皮层检测到有活动,因此把这种方法贬之为“误导”,不过被贬一方则坚称“从总体上来说,前额叶皮层对意识来说既非必要,也不充分,这和皮层后部完全不同。”看来这一争论还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因为现在对究竟什么是意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甚至对意识究竟包括哪些方面都没有共识。最近动物行为学家戴维・培尼亚-古斯曼提出意识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主观意识、情感意识和元认知意识。所谓主观意识是指主观存在感和具身的自我觉知感,所谓元认知意识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有认知能力的。[11] 但是显然,大家理解的意识并不仅限于此,同一作者在别处强调的意识的感知方面和理性方面,不过显然他并没有提及像在冥想状态下的意识方面。笔者不知道如何穷尽意识这把大伞下面的所有方面。所以如果当实验者都用同一个术语“意识”来指意识的非常不同的方面,那么就很难评判谁对谁错。
最后,笔者还想说几句肯定的话,有关前脑理论和后脑理论的实验事实并无多大问题,是意识实验研究上的一大进步,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些实验事实。对抗性合作也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新形式,应该用好这种形式,问题是如何选择好合适的对立双方,不要形成关公、秦琼争霸战,鸭同鸡讲。寻找度量意识的定量指标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必须认识到,意识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极多方面的对象,不可能定义一个指标全面刻画完其所有方面,而只能是刻画其某个方面,把个别方面等同于意识全体就必定犯错。目前,意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每个人讲的意识都是在自己语境下讲的,他们的实验也是在这种意义下做出的,由此引申出来的有关意识的“一般”理论,很难摆脱这种局限性,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现在有 20 种以上的“意识理论”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如已故江渊声教授所说:科学家要耐心些,不要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统一意识理论,虽然任何有一定实验根据的意识理论都可能有助于向最终目标前进有所贡献,至少引起人们的思考。
致谢:本文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曾多次和梁培基教授、Karl Schlagenhauf 博士、Hans Braun 教授和 Hans Liljenstrom 教授做了有益的讨论,梁培基教授还审读了全稿,并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Lenharo M (2023) Philosopher wins consciousness bet with neuroscientist. Nature 619:14-15
[2] Koch C (2004) The Quest for Consciousness – A Neurobiological Approach. Roberts and Company Publishers, Englewood, Colorado.
中译本:科赫著,顾凡及、侯晓迪译(2012)意识探秘 - 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年重版)
[3] Koch C, Massimini M, Boly M, Tononi G (2016).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Progress and problem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1567963).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7 (5): 307–321.
[4] Tononi G.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 Scholarpedia" (http://www.scholarpedia.org/article/Integrated_information_theory#Predictions_and_explanations).
[5] Dehaene S.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deciphering how the brain codes our thoughts. New York: Viking Press, 2014.
中译本:迪昂著,章熠译(2018)脑与意识:破解人类思维之迷.浙江教育出版社
[6] Finkel, E.(2023) Consciousness hunt yields results but not clarity. Science 380, 1309–1310.
[7] Fleming SM et al. (2023) 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as Pseudoscience. (https://psyarxiv.com/zsr78)
[8] 顾凡及(2021)有关意识的“困难问题”也许只是问错了问题。《信睿周报》第 57 期 11-14
[9] 顾凡及,施拉根霍夫(Karl Schlagenhauf)著,顾凡及译 (2019)《意识之谜与心智上传的迷思:一位德国工程师和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系列丛书,上海教育出版社。
[10] Odegaard (2017) Should a Few Null Findings Falsify Prefrontal Theories of Conscious Perception?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7(40):9593–9602
[11] Peña-Guzmán, D(2022)When animals dream : the hidden world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戴维・培尼亚-古斯曼著,顾凡及译(2023)动物会做梦吗?—— 动物的意识秘境。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IT之家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